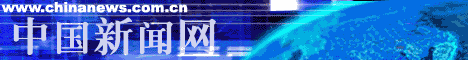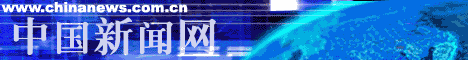近两个月来,北京大学教师人事制度的改革在华夏大地引发出一场大辩论,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分析认为,因为北京大学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一流大学,其改革的成功与失败,都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近日,留美青年学者李猛在《书城》2003年第8期上发表长文(约3.6万字),对北大改革方案给出了非常有见地的分析。本网现全文转载,供关心这次改革的人们思考。
如何改革大学? 对北京大学人事改革草案逻辑的几点研究
作者 李猛
一,改革与批评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人事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北京大学人事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张维迎教授撰写的“关于《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及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阐述了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方案的基本特征与设计原则,并试图回答来自校内外的许多批评,为关心这次改革的北大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了解这次改革的内在逻辑的绝佳机会。北京大学的这次改革,虽然第一稿在征求意见的时间安排上不免仓促,但能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在新的修订稿中吸收了其中的许多建议,集思广益,采用民主的方式来改善改革方案,可以说是北大管理上的一大进步。更充分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不仅有助于弥补方案草拟过程中由于未能充分征求不同学科学者的意见而对学科特点重视不够的缺陷,而且更重要的是,正象张维迎教授自己希望的那样,通过批评和反批评,才能“在广大教员中达成基本的共识”(绪论部分)。
新的征求意见稿的民主态度首先就反映在对第一稿中许多不够完善的措施进行了修改,去掉了一些与理不合、与法无据的措施,具体的内容,张教授已经扼要列举了。从张教授的说明来看,这些修改应该遵循了下述原则:“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坚定不移,但改革的步骤和具体措施必须稳妥、可行”。换句话说,只有更加稳妥可行的改革步骤和具体措施,才能让我们坚持改革的基本方向,尽快实现创办一流大学的目标,而相反,那些不顾可行与否、只从自己愿望出发的“改革”,只会使北大离创办一流大学的目标越来越远,而某些设计不妥的改革方案,甚至可能会破坏学术健康发展的氛围,危及北大已经很单薄的学术积累。改革的成败与否,并不取决于改革者的愿望。这些年来,北大的各级管理者,都曾努力尝试各种提高学校教学水平的改革。但至少根据张维迎教授的“说明”(特别是一,“为什么要对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下文引用只列“说明”每节的序号),这些改革都没能实现将北大变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所以我们才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张教授大概不会否认,以往改革的设计者乃至执行者,都至少和这个新的方案的制定者或批评者一样,希望北大能成为一流大学。但张教授认为,以往改革没有触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一),所以不够彻底,没能为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立基础。如果说张教授对以往改革的批评并非反对改革的话,同样,那些反对张教授设计的改革方案的具体措施乃至整体设想的教师或校外其他人士,也不一定是在反对改革本身,而是希望能够通过深入细致的讨论逐渐弄明白旧体制的弊病是否是“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端,因此是否能够通过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主持设计的这个方案来一举革除。正如张教授明确表示的,北大的这次改革之所以和以往不同,和别的学校不同,就在于它希望“找到一个既兼顾眼前现状,又具有长远生存和竞争能力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一),而不是不断进行修修补补的改革。所以,改革就必须抓住北大现有问题的症结,才能实现改革的目标。
正是因为这次改革对于北大的未来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北大的教师才“高度关注”这次改革方案的制订和修改。这些“大学教员,作为中国社会最有知识、最知书识礼的人”,尤其是中青年教师,长期以来为北大的事业做出了许多牺牲。其中的优秀人才之所以留在北大,没有选择出国或是下海,在收入水平和研究条件都不够理想的情况下,始终在北大坚持从事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并不是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而他们之所以选择北大,也并不是因为北大能提供最好的“铁饭碗”(不用说企业,其他许多高校都能提供更高的职称和收入),而是因为北大尽管存在诸多未尽如人意之处,却是他们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真正希望。“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因此,对于这些人,如果为了实现作为他们理想的北大事业,需要付出他们本人作为代价,他们并不会仅仅因为个人利益受损就反对改革。但如果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结果却是毁灭了他们为之倾注了全部热情的这项事业本身,摧残了他们做出巨大牺牲竭尽全力继承和发扬的中国学术与文化,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无动于衷。张教授也承认,现在的北大,并非没有这样愿意献身学术又颇具才华的人才,只是因为现有北大落后的体制,才不能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需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将他们与北大中青年教师中相当一批才华与敬业程度和北大不相称的人区分开。因此,无论对于这些优秀的中青年教师,还是对于许多关心北大的人来说,问题都不在于是否改革,而在于如何改革;不在于是否反对这个改革方案,而在于现有的方案是否真的能够找到一个办法,将学术上的优秀与平庸区分开,让北大现有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并吸引更多的一流教师。
张教授牵头的人事改革工作小组设计的这个方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了两部分内容:遵循竞争逻辑的聘任晋升机制和针对学科的“末尾淘汰制”(二)。为什么这样的机制就是“一个既兼顾眼前现状,又具有长远生存和竞争能力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从而能成为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体制基础,作者的“说明”并没有给出一个系统的论证。当然,这份“说明”不是学术报告,而只是对“改革方案的基本精神”的说明,因此缺乏对改革逻辑和思路的系统阐述也有情可原。但回答“如何改”的问题并不能解决“为什么这样改”的困惑。我们当然希望张教授等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会另外撰写文章来系统论证北大教育改革的逻辑。不过在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文章之前,我们这里只能根据张教授自己精心撰写的“说明”来努力理解这份改革草案的“精神”,通过张教授对“如何改”的说明来把握这个改革方案的实际运作形式,从而理解在张教授的心目中为什么要这样改。
二,改革的依据(1):企业的逻辑与大学的逻辑
张教授论证这些机制的第一个依据是“企业”改革。对于一位精通企业理论的经济学家牵头起草的方案来说,这原本不足为奇。作者频频诉诸处于市场竞争中的企业来为北大采取竞争机制的人事制度改革进行论证,旧北大被比喻为落后的国有企业甚至家族企业,只有将她置于市场的风浪中,才能避免破产的命运:
(1)“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在就业市场上已成为一个普遍接受准则和文化观念,‘铁饭碗’和‘大锅饭’的体制在许多行业已经被打破,现在,大学已成为少数几个仍然保持‘铁饭碗’制度的行业。我们现在所做的改革不过是企业和政府部门早已进行的改革”(一)
(2)“那些不改革的大学将会在竞争中衰落甚至被淘汰。这就如同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样,现在破产的国有企业多是那些不认真改革的国有企业”(二)。
(3)“在企业改革中,许多月收入只有几百元的工人也不得不下岗……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大学教员作为中国社会最有知识、最知书识礼的人,必须有铁饭碗的保证,不能分流。这样的要求对其他社会成员是没有说服力的,也是不公平的”(一)。
(4)“那我们办博士项目就没有多大意义,就像一个钢铁企业只为自己生产钢材一样,更不用说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了”(六)。
(5)“如果一个大学不是以外部市场为主,而是以内部市场为主,一个人一旦进入就不出去,不论水平如何都能爬台阶当教授,而外部的人再优秀也进不来,这个大学实际上就变成了先来者的家族企业,永远不可能是一流的”(八)。
(6)“在计划体制下,教员与学校之间只有工作和隶属关系,没有正式的合同,但正像有些教员正确地指出的,这种工作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隐性合同。但是,隐性合同并不是不能解除。事实上,整个国有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新的就业合同替代原来的隐性合同的过程”(十四)。
(7)参考:“不赚钱的组织是‘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张教授如是作答,颇有一番回味。大学作为一个创造知识和传递知识的机构,其两个难题就是,它既难以创办,也难以垮台。当大学的品牌创立起来,每个相关的人只会竭力维持这个品牌,在这种‘善良愿望’之下,它的问题就不容易暴露;所以,大学改革的压力远不及商业性组织(企业)”(张教授6月12日“关于大学改革的演讲”)。
多少出乎意料的是,在北京大学同时公布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全文没有一处提到“企业”,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企业的逻辑作为大学改革的根据并不需要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而只需要出现在对文件的“说明”中。不过,或许更出人意料的是,仔细阅读“说明”会发现,在张教授的笔下,“企业”不只是大学改革的样板,更多却是大学运作逻辑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说“更多”是有依据的,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企业”在“说明”全文中共出现27次,其中用来论证这个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合理性的共有7处,而其他20处都是“说明”企业与大学的逻辑是不同的(其中有3处是出现在企业可以帮助安置大学淘汰人员的讨论中,事实上,正象我们看到的,竞争激烈的企业能够安置相对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大学中的淘汰人员,正是因为二者的机制或逻辑不一样):
(1)“学术竞争与企业竞争有所不同,如果一个企业不用优秀的人,市场竞争很快就会把他淘汰出局;但大学声誉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一个新建立的大学要在短期得到社会的认同是很难的,而一旦建立起一个好的声誉后,短期内也不可能垮台,这给老大学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就生存而言,大学面临的竞争压力远远小于企业”(二)。
(2)“大学的稳定性为终身教职提供了可能。企业的不稳定性使得企业不可能提供这样的制度,好在市场竞争使得企业也没有必要采纳这样的制度”(二)。
(3)“事实上,自古以来,学术界都是外部市场为主,内部市场为辅。在西方,企业用人多是内部市场为主,外部市场为辅,但大学正好相反……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是由学术市场和大学的特点决定的。”(五)。
(4)“有些学科的竞争对手是企业,企业的工资比我们要高得多,我们必须提供较高的收入才能吸引到人才。但是,必须认识到,大学永远不可能与企业相比。大学教授的平均工资比企业界低,这在全世界都一样。这也是一个自选择机制,如果大学的工资与企业一样,就会把一些本来没有兴趣搞学问的人也诱惑到学术市场上来,挑选教员更为困难。有了这种差别,那些对学问本身兴趣不大的人就会自己选择去企业找工作。”(六)。
(5)“有人可能会说,企业界想要的人也是大学里最优秀的人。其实不是这样。学问做得好的人通常都不适合在企业工作;反过来,许多学问做得不好的人到企业界却如鱼得水”(八)。
撇开一些具体论述是否准确的问题(比如是否自古以来学术界都是以外部市场为主呢?柏拉图创立的雅典学园的主持人都是院内继承的,中世纪大学的教师也很少采用完全公开的外部市场,不过这样的历史知识自然不是关心知识创新的新方案在乎的地方,我们可以暂且放在一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可以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学术,不是从来如此,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如此,这一点张教授自己非常清楚),我们会发现这些强调大学与企业不同的段落几乎都出现在“说明”最关键的地方,也就是“说明”用以打消大家对这个改革草案的疑虑的地方(“关于新体制的基本特征和设计的理由”,“关于招聘和晋升中引入外部竞争机制的问题”,“关于留不留本院系应届毕业生的问题”,“关于出路问题”)。深谙企业理论的张教授强调,“学术竞争与市场竞争不一样”,在用人方面,学术市场的形态与企业不同,而且,两者用以评价人才的标准也不同,“大学的稳定性”要求大学必须采用“不稳定”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之外的逻辑。张教授甚至特别诚恳地告诫大家:“必须认识到,大学永远不可能与企业相比”。如果是这样,读者不免会问,采用与大学逻辑如此不同的企业逻辑如何能够证明现有体制的缺点和新方案的优点呢?
不过,有人或许会说,企业的逻辑尽管和大学教育的逻辑不同,管理企业的逻辑却与管理大学的逻辑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设计大学管理的改革方案时可以以企业逻辑为基础。但张维迎教授就是一个在经济学领域颇有造诣的教授,按照他本人阐述的逻辑,似乎由他来设计北大改革方案,而没有请一个在企业界如鱼得水的人,我们的教育学院也没有合并到光华管理学院中,说明管理大学同样与管理企业的逻辑多少有些不同。张教授其实和那些批评他采用企业逻辑来指导大学改革的人一样清楚,企业和大学是不同。只不过,张教授虽然可以一边强调企业与大学在逻辑和机制上的差异,但却仍然坚信企业和企业式的市场竞争的逻辑应该成为改革北大人事制度的基础。
那么是否张教授认为大学与企业的差异只是因为大学在竞争机制的建立上落后企业,而好的大学就是最接近市场逻辑支配的企业的大学,好的大学体制也就是最接近企业用人体制的体制呢?但这恐怕误解了张教授的想法。毕竟作为张教授改革方案核心的“tenure-track”(“终身教职序列”或简称“终身教职”)的制度就与企业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很不一样。如果完全根据后者的逻辑,就应该废除“终身教职”的制度。但在美国,恰恰是那些水平较低的社区大学较多雇佣非“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而一流大学却全都采用“终身教职”制度。近些年来,由于经费等方面的原因,连美国自己的学者也慨叹,“美国大学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参见杜克大学Stuart Rojstaczer 199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Gone For Good: Tales of University Life after the Golden Age)。在这种状况下,这些一流大学也开始聘用一些非终身教职序列的教师,不过这些教师大多从事学术地位较低的工作,而且许多教师也只是把这样的工作看作是进入终身教职序列之前的过渡。事实上,如果在大学用人体制上,市场竞争机制的逻辑就是比所谓“大锅饭”制度好,那么与其费尽力气证明教授拿到终身教职之后(也就是在基本摆脱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仍然会努力工作,为什么不简单地对全校教师一视同仁地采取3年一个合同的聘用机制呢?毕竟用“习惯”、“惯性”或“脸面”这些理由来证明这些终身教授们会象没有终身教职一样继续努力工作,大概不象是设计机制,更像是祈祷。因为如果这些原因会发挥作用,现有体制同样也可以有效运转。难道现在的教授就不顾“脸面”了吗?
那么为什么要采取终身教职制度改革北京大学呢?张教授给我们的理由再次是企业与大学不同。张教授一再强调企业与大学的差别在于“学术市场和大学”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差别尤其体现在“用人”机制上。而用人的机制正是这份北大改革方案的焦点,这难免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张教授一边在改革草案的关键机制上强调大学和企业在逻辑上的差别甚至对立,另一边却坚持用企业改革的逻辑来衡量北大这次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机制呢?尤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在谈及现有体制的用人机制或者批评者提出的以副教授为起点的终身教职制度时,张教授就称这样的体制为“铁饭碗”,是计划经济的“漏网之鱼”(张教授6月12日“关于大学改革的演讲”)。似乎言外之意,只授予正教授以终身教授就使新体制完全摆脱了“铁饭碗”。难道,教授的终身教职或长期教职就不是一种“铁饭碗”吗?这样的论证,恐怕缺乏学术上的诚实态度吧。
如果大学应该在有些地方仿效企业,有些地方不这样做,那么决定是否这样做的逻辑就不应该到企业那里找,而应该真正严肃地考虑大学本身的特点。在现代教育体制中,考虑大学研究院的体制(这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体制)确实不能脱离“竞争”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张教授对学术体制与企业体制的不同特点的强调,那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到企业式的市场竞争之外思考学术竞争自身的逻辑。即使北大的改革草案希望利用学术竞争的市场逻辑来激励与筛选更优秀的人才,那么也不应该简单地将完全不合学术规律的企业竞争法则拿来衡量大学,更不能利用大家对北大现状的不满,就简单地把北大的问题理解为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这是好的修辞学,因为似乎大家都对国有企业痛心疾首,而且这些年的改革尽管没有成功地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至少说服大家“相信”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不过北大的问题不能靠国企改革的修辞学来解决,而是需要找到真正符合所谓学术本身规律的“竞争”机制,而且,如果张教授确实希望这次改革不是一次“休克疗法”,那么这样的竞争机制,还必须真正严肃考虑与中国整体学术体制,而不仅仅是北大的现有体制的“衔接问题”,否则这次在跑步中进行的手术,弄不好会因为各种“排异反应”而送了人命。
不过,或许我们把张教授用来说服大家的修辞学误当作他的真实想法了,其实这份改革草案背后的依据并不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作为教育上的落后者,我们必须通过仿效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机制来改革自己的机制,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已经找到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学术人才的激励与筛选的竞争机制,北大的改革就是要将这样的机制移植过来。
三,改革的依据(2):向哈佛大学学习
如果笔者没有弄错的话,哈佛大学在张教授的“说明”中共出现了10次之多。哈佛大学几乎成了教育的样板,西方教育乃至美国教育的理想标准。其他国外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即使提到,也不过是用来证明它们和哈佛一样,或者象北大一样,也在努力向哈佛看齐。
这样的做法无可厚非,一方面,哈佛大学在美国和世界上的影响,使哈佛大学似乎理所当然地成为学习西方先进办学经验的理想选择,另一方面,哈佛大学在中国学生和社会中的光辉形象可以赋予张教授的改革草案以巨大的吸引力。想想看,如果北大变成哈佛,或至少和哈佛比肩(六),那对于崇拜哈佛的中国学生和教师来说是多大的荣耀啊!可是北大能变成哈佛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看看哈佛或者美国其他的著名大学是否吻合张教授设计的北大改革草案。
根据张教授的“说明”,北大人事制度改革草案的核心是“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加上学科的“末尾淘汰制”。据张教授说,“无须讳言,这两个特征结合起来基本上就是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tenure-track’制度。这种制度也被称为‘up—or—out’(不升即离)合同,在一些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当然,投资银行一般没有终身职位“(二)。这里,我们首先讨论“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
这里,首先有必要指出一点,在美国讨论高等教育的文献中,终身教职(tenure-track或tenure/probation)体制和短期合同(term contract)制度往往是大学雇佣教师时可供选择的两套不同方案。1990年代以来,由于大学资金紧张等原因,终身教职的问题再次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广泛争论的议题。拥护和反对的双方围绕学术自由,工作保障以及参与学校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双方的焦点就是在这些方面究竟是终身教职制度更好,还是短期合同制度更好(参见William Mallon在2001年出版的Tenure on Trial一书第二章中所做的综述)。而张教授设计的方案其实是一个糅合了终身教职与短期合同两套体制的方案,将这样一个方案直接冠以“tenure-track”的名目,多少有些混淆视听。
在张教授具有独创精神的方案中,一个博士,如果要获得终身教职,最长有可能需要6个合同,经过6次合同评审和2次职称评审,即使最快,他也需要至少2个合同,经过4次评审。与纯粹的短期合同制相比,这样的制度可以说是既没有这种制度的拥护者赞赏的灵活性,又最大程度增加了合同制度反复冗长的评审程序方面的缺陷;而与美国一流大学实际采用的“终身教职”制度相比,北大的方案在实质上缩短了教授在终身教职阶段的工作时间,而变相延长了试用期的长度(最长可达18年),大大减少了终身教职制度保护和鼓励教授进行具有独创性的自主研究的优势(这原本是设计这一制度的一个主要考虑)。也就是说,张教授设计的这个方案几乎集中了两种体制的主要缺陷(参看Mallon综述对批评tenure和contract两种体制缺陷的讨论)。如果我们考虑到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在设计获取终身职位的试用期(往往6-7年)方面,还要涉及tenure clock的停摆等复杂问题(比如女教师休产假),这个新草案设计的晋升制度,似乎复杂得根本无法执行,或者按照中国的惯例,充满了各种讨价还价的学术政治活动的空间。恐怕未来北大教师的主要精力不是从事科研或教学,而是学习应付这个无限复杂的制度。
那么,为什么要在张教授自己称为“美国大学普遍实行的‘tenure-track’制度”上,又再叠床架屋地加上一套颇为系统的“短期合同”体制呢?因为“说明”有意回避了声称学习美国先进经验的“新方法”与美国高等教育主流体制实际上的差异,也就自然不会交待这样做的原因。不过,我们有理由猜测,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新体制对市场竞争逻辑的偏爱。换句话说,张教授设计的北大体制比美国高等教育体制更加强调竞争。通过短期合同体制不断给年轻教师施加压力,以促使他们更勤奋地工作。这种想法背后其实就是一套企业竞争的逻辑。换句话说,张教授在理解美国的教育体制的时候,仍然坚持从他已经断定和大学逻辑迥异的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从不同地方挑选出一些制度,组合成北大的“新方法”。所以,他在“说明”中才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在北大引入他这种tenure-track制度,是为了竞争,并通过竞争来促进学术自由(参见张教授在北大校园网回答问题)。
事实上,在美国同样也有一些学者象张教授一样强调对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动进行更具竞争性的监督,以避免出现“冗员”(deadwood),不过,这样的学者往往明确主张用可以不断续签的短期合同来代替传统的终身教职制度。张教授一边接受这些学者的逻辑,一边却大张旗鼓为终身教职制度辩护,而只对“教学效果好但科研能力差”的专任教学型教师采取更符合他的市场竞争逻辑的纯粹“合同制”(九),似乎忘了这里面有着不小的矛盾。
不过,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这种试图采用短期合同来提高学术活动绩效的做法,来源于“太把教科书里面的经济理论当真了”(taking textbook economic theory too literally),而实际上,一些长期关心终身教职问题的美国教育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经验研究。他们通过对一些大学的分析证明,如果不断评审短期的合同,因为这种评审对于大学来说成本极为高昂,短期合同制最终往往流于形式,教师淘汰率比终身教职序列制度还低(参见Matthew Finkin所著The Case for Tenure一书,特别参见The Economics of Tenure一章中论Term contracts as an alternative to Tenure)。对美国高等教育问题颇有研究的著名社会学家Edward Shils曾做过简单的估算,即便采用5年的较长合同期,在一个由15-20名教师组成的系里,如果认真进行评审,大概教师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要花在评审上(“Academic Freedom and Permanent Tenure”,收入Edward Shils有关美国高等教育的文集The Order of Learning: Essays on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根据Shils的逻辑,大家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普遍采用3年制合同,教师超过80人的北大法学院的合同评审情况。事实上,张教授自己也暗示,北京大学未来的大部分合同评审都不过是“形式”:“除了晋升和最后一个合同期,其他合同期满后续约的条件以达到表现基本满意即可”。如果大部分短期合同都没有什么监督、筛选和激励的作用,这种终身教职加上短期合同的制度除了增加“形式主义”,养成教师对评审活动的不认真态度,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不直接采取美国大学真正普遍实行的,也更简便有效的终身教职制度呢?
其次,正如有些批评文章已经指出的,北大的改革草案(至少第一稿)与英美大学普遍采用的终身教职制度的另一个重大差别是终身教职制度保护的教师在范围上大大缩减。新发表的第二稿对原稿第十一条的修改(有关给予副教授长期职位的规定)已经承认了这一点。但张教授似乎仍然强调他设计的方案在美国也不乏先例。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统计数字,就知道这个先例所占的比例。根据AAUP(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在2003年发布的统计(参见Academe 2003 March,或参见同时的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在美国大学的正教授中,进入终身教职序列的有98%,获得终身教职的有96.6%,而在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当中,进入这个序列的有95.9%,而拿到终身职位的有84.7%,甚至在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大致相当于北大的讲师)一级,也有13.6%的教师获得了终身教职。显然,美国大学中绝大多数副教授是拥有终身教职的。
当然,正象张教授说明的,改革草案的起草人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但因为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而在初稿中没有采取美国比较通行的制度(三),而且即使在修订稿中也认为不应该马上采取这一制度,而是交由学校在未来酌情处理。张教授的这一“说明”至少表明,甚至在作为美国大学用人制度最核心的终身教职体制方面,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套用美国的方法,因为这样做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其实,张教授的草案对中国学术界现状的考虑并不仅限于这一例。比如,学校在新的人事体制中仍将严格控制各系正教授的指标(十)就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既然如此,那么在决定现有人事改革体制成败的许多关键机制方面,改革草案是否同样充分考虑如何根据中国学术界现状设计出既符合改革方向,又现实可行的步骤呢?
例如,美国式的大学竞争—流动体制是建立在非集中化的大学体制(decentralized universities system)基础上(参见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Derek Bok在Higher Learning一书中对美国高等教育特点的分析,这一特点几乎是每本讨论美国高等教育体制的书都会重复的一个前提),而欧洲的情况就大不相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国家资金资助的水平,教师更类似国家公务员,而非企业雇员,所以很难简单套用具有高度“竞争”形态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任何对中国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不难发现,中国大学的现状与欧洲更类似一些。对这一点张教授毫不讳言,甚至一再强调这是北大改革的一个重要理由:如果不改革,就无法再拿到国家的巨额资助(一);而北大改革的成功,也会帮助北大从国家获得更多的资助(六)。看来,张教授是非常满意中国的欧洲式教育资源分配体制,而且他的改革草案也在资源上极度依赖这样集中分配资源的“计划”体制。尽管如此,张教授却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可以采用美国式的竞争流动机制来解决北大的问题,甚至可以借此强化北大这种欧洲式的政府庇护大学的模式。这就难免让人感到奇怪了。毕竟在一个没有美国式的教育“多极化”、“非中心”的大学格局中,如何借助美国式的竞争体制来管理大学,恐怕哈佛大学校长也难以回答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
根据张教授提倡的这个逻辑,促进中国教育体制美国化,从而使北大有机会学习哈佛的最理想办法首先就应该是减少政府对北大的拨款,将拨款向水平较低而且又缺乏足够资金支持的其他大学倾斜,改善这些学校在图书馆、实验室等硬件条件方面的劣势,从而为人才的竞争和流动真正提供牢固的硬件基础。不过,北大清华这两所受到垄断性支持的大学自然不愿意采取这样的做法,而理由也很充分,应该集中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财力,集中办好几所大学。这样的逻辑自然有其道理,毕竟一个对美国高等教育基础条件有所了解的人的人都知道,以中国现有的教育资源情况,要达到美国州立大学在教学科研的硬件设备上的条件,即使只资助北大和清华两三所大学,恐怕也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但这就意味着,除去几所幸运的大学之外,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根本不具备参与大学竞争和流动的基本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鼓励流动的措施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学术人才的培养,损害学术的发展。比如,禁止北大各院系留自己的博士生,往往结果是强迫这些最有学术潜力的年轻学者到与北京大学有相当差距的学术环境中工作。根据张教授自己对大学等级制的描述(“二流的大学之所以是二流的,是因为他们只能招聘到二流的学者,也只有二流的学者才愿意进入这样的学校。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结果”。五),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和水平较低的学者在一起进行非学术的竞争,意味着人文学科的学者往往会在一个严重缺乏图书资料和优秀本科生的大学中进行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而理工科的学者难以进入拥有更多研究资金和更好试验设备的实验室,更少机会从事基础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而不得不转向应用研究。也就是说,这些博士生在博士后期间(讲师甚至直至副教授期间)的训练将更不适于在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中的工作。而这等于说,除少数较少受这些基础条件影响的学科,国内大学培养的博士基本上不可能再回到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任教,结果只有吸引从海外大学归来的学者来填补新方案苦心腾出的空缺。
缺乏美国式的竞争与流动机制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并不仅限于此,缺乏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另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竞争式的筛选-激励机制能够发挥作用,必须有一个成本很低的评价机制。这种评价机制是竞争和流动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而不是相反。事实上,这一点也在总体上限制了单纯的市场竞争在大学教育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哈佛大学前校长Bok就曾指出,评价高等教育水平的困难是“竞争在高等教育中不能产生最优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美国如此,中国就更是这样。
张教授指出,北大旧的晋升体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教员招聘和晋升不能主要依据学术标准,而是人情、关系、资历和以往申请次数等非学术标准,因此需要引入外部市场,通过市场来给个人标个价码,优秀人才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当我们在市场上买到一台电视机时,我们只知道它的生产厂家,而不可能知道制造它的工人是谁,但是,当我们在杂志上看到一篇学术论文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知道它的作者是谁,我们一般并不在乎这个作者在那所大学工作。这一点决定了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学者可以有统一的市场价码,优秀的人才不会被埋没。外部市场也是显示个人价码的重要机制,竞争的学者市场可以给每个人最正确的评价”(五)。这里的论述表面上似乎论证了竞争机制可以成为学术评价方面非常有效的机制,但仔细考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再次偷换了有关的市场概念,陷入了典型的循环论证。如果我们能够象张教授断定的那样比评价电视机更容易地评价一个学者的水平,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进行如此复杂的人事制度改革,传统的晋升和招聘体制同样可以采用这样严格而简单的标准来实现筛选人才的目的,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多不够格的教授了。
但事实上,虽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一篇文章的作者是谁,但却无法同样轻易地判断文章的水平如何,究竟是重复还是创造。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即使同属一个大的学科,不同分支的学者也很难清楚地了解彼此工作的价值,更何况学术观念相差甚远的不同学科之间。一个经济学的教授有时会觉得,研究中古音韵学的老师从事的工作与国计民生没有直接关系,转化不成经济效益,是毫无意义的活动,而反过来,哲学系的教师也可能认为象管理学院这样的地方,根本就是在卖文凭,没有一点学术味道。如果让抱有这样误解的学者彼此评价,恐怕难以评聘到该学科真正优秀的人才。而美国的竞争和流动机制能够相对运行得比较好,就是因为尽管学术评价存在这么多的困难,美国仍然建立了学界公认的评价机制,在发表学术成果的不同刊物的水平和引用机制方面都有大家比较公认的标准,不会让学术成果由是否能在学术之外的市场上找得到买主,或者作者是否有广泛的知名度这些与学术无关的因素来决定。
即使在科学成果应用速度日益加快的今天,作为研究型大学主要特征的基础性研究领域,其成果往往都无法由学术之外的市场来评价,新闻媒体也没有能力充当学术水平的裁判。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近年来国内科学界过于强调SCI论文数量,喜欢选择耗资巨大、名声响亮的科研课题,但却对真正具有开创性和基础性的研究十分忽视,SCI论文数逐年上升,但高水平论文数上升缓慢,论文引用数也没有多少改进(参见中科院邹承鲁院士的“一等奖为何连续空缺”一文)。这些都是学术逻辑之外的经济政治力量过多干涉学术的结果。如果由市场来决定学者的优劣,恐怕象2002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Syndey Brenner这样的学者都会被北大扫地出门,毕竟他从1960年代开始从事的默默无闻的线虫研究,在当时看不到任何应用价值,也远不如耗资巨大、在中国炒得火热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来得有新闻价值。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现在还远没有建立起来客观自主的学术评价机制,在文科,即使象《中国社会科学》这样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并非没有争议;在理工科,科研经费的申请经常受课题学术价值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中,学术的逻辑往往没有经济的逻辑和政治的逻辑声音大。张教授设计的人事体制,不仅没有改善这一点,而且这个方案本身就是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取代学术逻辑的结果。这一点如果没有改变,新的人事制度不过是将讨价还价的价码或风险提高,将报价人的范围扩大,但并没有改变讨价还价赖以存在的基础。有理由预见,在新的体制下,因为招聘和晋升所进行的各种学术游说活动会进一步从校内扩展到校外,甚至从中国扩展到全世界。这种竞争,其实在现行体制下就存在,但在未来体制下会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从而进一步毒化学术气氛,淘汰那些一心做学问、而没有钻营能力的教师,难道这就是北大的改革要求教师付出的代价?
当然,张教授可能会辩称,他的真实意思不是说北大的新人事体制可以利用比电视机或矿泉水更简单的评价机制来实现(那不过是象“说明”中的许多其它论述一样,是说服大家的修辞学,不是他的真实想法),而是通过这样的改革将北大教师放在市场上来标价,买的人多就是高水平的,相反就是低水平的。这里我们姑且不论在这样的机制中是否会有大器晚成或超出他们时代太多的学者更难生存的问题(毕竟我们的制度经济学家崇拜的Coase教授发表的重要文章“厂商的性质”,根据他自己的回顾,就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没有受到充分重视,这个时间已经远远超出了张教授认为一个教师证明是否够格的时间,参见四),而是关心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这样的体制是否可以在中国凭空建立起来。
首先,我们需要澄清一点,一件东西是否价值高,并非因为有“市场”,而是由经济学家喜欢谈的“偏好”决定。“偏好”本身对于市场来说是外生变量,而不是内生变量。换句话说,市场只是揭示了人们已有的偏好,从而根据供需关系来决定一个东西的市场价码。在基本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本身并不能增加对一个东西的“需求”。因此,市场化程度高,并不能自然使一个东西的价值升高。相反,对于就业市场或者说劳动力市场来说,如果“市场化”程度高是指竞争更不受各种壁垒的限制,从而竞争也更“公开”,那么,相应职业的供给弹性会很大,简单地说,就是这个职业谁都能干,因此,这个职业的收入和社会威望都会比较低。而收入和社会威望比较高的职业,往往是那些从业人员可替代性差,也就是说,很难找到代替他们的同样优秀的人才。这些行业,往往利用“证书”和“资历”等手段建立各种壁垒,从而不那么“市场化”。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中的老生常谈了,也符合我们的常识。在当代中国,竞争比大学教师激烈得多的民工的社会地位相对比大学教师低得多。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始终在职业威望调查中居于前列,但他们并非靠市场的竞争机制不断筛选出来的,而是“铁饭碗”。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人的地位最高”,并不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文人的统一市场”,而是因为人们重视“士”在礼乐征伐方面的作用,而这些其实不过是本就出于“王官”的“士”在新型的国家形态中通过继承和重塑传统的文化理念来发挥关键的政治功能。“士”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就象今天大学的作用一样,恰恰不是听从社会经济逻辑的摆布,而是在文化和思想上引导社会的变革。同样,当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按照张教授的说法,算是彻底取消了这个“文人市场”,不过似乎中国文人的地位并没有从此降低,他们出将入相,是“士农工商”之首,而没有象在今天的“文人市场”中由“商人”来给自己标上几百万的价码。我们今天的大学当然不是要回到古代,但不能曲解古代来为自己辩护。
张教授主张“公开”的原则,而且相信“竞争”可以激活人事体制,其实并不是主张拆除大学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壁垒,相反,新体制在这些方面比旧体制要求更严格(例如要求“新聘教师应当具有博士学位(或本学科最高学位)”,甚至考虑规定从博士到获得副教授的最短年限,参见三)。因此,张教授主张的并不是完全公开、没有壁垒的竞争,而只是通过不同高校之间争夺优秀教员的竞争机制来确立他们的相对水平。好的教授自然会有别的大学花大价钱来挖(张教授举的例子大都属于这一类)。这个“外部市场”可以简明地给优秀人才贴上了标签。也就是说,一个优秀人才,也就是更可能被其他学校招聘的人才。不过,张教授设计的晋升和流动体制的核心是针对副教授和讲师,而不是针对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而不同大学争相聘请的更多是已经成名的教授,而不是讲师或副教授。换句话说,恰恰在张教授设计的体制中获得终身教职,从而摆脱竞争压力的学者,最可能由张教授的市场标上清楚的价码,而相反,置身竞争机制核心的讲师或副教授,往往缺乏张教授喜欢提及的知名度(除非学术市场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反而是讲师和副教授名气更大,但如果这样,按照张教授的观点,恰恰证明这样的体制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未能按声誉建立学术等级。此外,即便有个别讲师或副教授“名气”很大,根据张教授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根据特例来制定制度)。
简单地说,这套争聘教授的体制,根本就不能提供一套有效的学术评价机制,来决定哪个人可以晋升教授,而这恰恰应该是终身教职这种晋升评聘体制最关键的环节。这一点,熟悉美国大学教师获取终身教职过程的人都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会借助校外的专家推荐信非常重要,但本校,尤其是本系相关专业的教授往往有决定意义的发言权,因为只有这些教授才对该教授的教学科研能力有更全面的了解。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法学教授Matthew Finkin在The Case for Tenure中对Jackson诉哈佛大学一案的讨论,作者详尽描述这位哈佛商学院的女学者两次申请终身职位的整个程序细节),不知道为什么熟悉美国大学体制的张教授却有意含糊其词,将“名教授”的“竞争”与聘任合格的优秀教授的问题混为一谈。或许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在北大从事科研教学的副教授或讲师极少能晋升正教授,北大未来的终身教授另有来源。
虽然,这种“挖角儿”式的竞争,在国内尚未能依靠学术逻辑本身形成权威评价的情况下,并不能自动建立一套成本低廉的评价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年轻学者就完全不能脱颖而出,如果一个讲师,能够在权威的《自然》(Nature)或《科学》(Science)上发篇文章,按照张教授的标准,自然可以证明他的价码。不过,这不过是在借用美国的学术评价体制,换句话说,正象聘请海外教授进行评审一样,张教授在改革草案中涉及的竞争和流动机制,都是嫁接在国际,尤其是美国,已有的评价体制上。这其实才是张教授为什么相信即使国内没有实行相关的配套改革,“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也能“成功”的奥秘。这一点可以从“末尾淘汰制”的引入更清楚地看出来。
四,为什么要“末尾淘汰”?
张教授的改革草案中,有一条非常关键,但却容易受到忽视:单纯的“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即给正教授以终身教职,让副教授和讲师通过短期合同和有限次数的晋升机会来实现竞争和流动的tenure+contract体制)并不构成tenure-track制度,而是与学科的“末尾淘汰制”“这两个特征结合起来”一起构成这样的制度的核心(二)。
但美国大学是否广泛采取末尾淘汰制呢?哈佛大学在工科方面长期位于全美前10名之外,但似乎并没有取消工科的打算。毕竟强如哈佛,也不能做到所有学科都排在10名之内(参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出版的《全美最佳研究院》),或者按照某些更权威的标准,都被评定为“杰出”(outstanding)。哈佛大学也有一些学科算不上非常好(very good)或“强”(strong),只是“好”而已(参见由权威的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组织的专门委员会出版的Research-Doctorate Programs in the Unite States)。而且就整个院系的排名来说,平均能做到“强”以上的,在全美也只有9所大学(参见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在2002年出版的《德美高等教育趋势》中的研究文章)。如果根据张教授的末尾淘汰制,即使采用较为宽大的10名标准,怕是连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杜克大学这样的名校也要解散一半以上的院系。
事实上,美国许多知名大学在取消或重组学科方面,除了受到经费紧张的压力外,主要依据的并不是该学科的排名是否在前列这样简单的“竞争”逻辑。芝加哥大学近些年来在重组学科方面一个比较大的举动,就是取消了教育系。不过这并不是芝加哥大学的教育系被“末尾淘汰”了,相反,芝加哥大学的教育系,在教育学界长期以来都有相当高的声望,也一直排在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前十位,但当时主持社会科学的教务长认为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不宜单独组成一个学科。换句话说,取消该学科的原因(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理由),是学术的考虑,而不是单纯竞争的逻辑。这正是美国主要大学合并和重组学科最主要的原因。
不仅学科的“末尾淘汰制”并非美国大学的主要特点,而且事实上,这样的政策也很难执行,不用说解散英语系,即使解散排名比较靠后的西班牙语系,哈佛大学也会在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张教授自己也隐晦地承认这一点(“即使你不担心你的院系被解散(因为它太大了,无人敢解散)”,七),那么为什么张教授还要坚持把它作为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呢?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体制”对于张教授的“草案”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张教授需要这个机制来弥补改革草案在逻辑上的根本缺陷。
围绕张教授的改革草案的争论,大多集中在改革草案设计的晋升等学术机制是否比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旧的体制理想,或者改革是否脱离中国国情等方面。不过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搞清楚一点,改革草案设计的学术体制究竟会怎样运作。毕竟,如果我们要比较两种体制,不应该拿一个体制的“理想状态”与另一个体制的“现实状态”来比。如果单论“理想”的话,旧体制同样可以找到许多无人能够反驳的宏伟目标,但我们却对旧的体制十分不满,认为这样的体制其实很难实现它自己宣称的理想。同样,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新设计的体制宣称它能克服旧体制的缺陷,就误以为它在现实中真的能够克服这样的缺陷。一个好的社会科学家就在于他在体制尚在纸面上的时候就能够看到它在实际运作中的样子。
作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似乎比大部分批评者对新的体制究竟会如何运转更清楚一些。在解释为什么北大在仿效美国的终身教职制度的同时却仍然要对名额进行限制时,张教授的理由非常清楚:“各院系评职称的过程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有许多人一直在等着升教授,如果现在就取消名额控制,恐怕用不了两年,大部分教员都成正教授了。这将与我们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不是学校不相信院系领导的品质,但学校有理由担心,院系领导顶不住压力。所以,名额限制现在还不能改。现在只能是名额和质量双重控制”(十)。显然,张教授很清楚,即使实行了新的晋升评聘体制,由于缺乏客观可行的评价机制,各院系仍然会依照旧的原则来评聘。甚至不能留北大博士生的规定,也很容易通过在外校做一两年博士后的办法规避掉。各院系的领导还是会“任人唯亲”(六)。而且在北大可能长达十几年的工作经历同样会形成新的“关系”,从而使制度的改变不过是从一种形态的“熟人”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熟人”(五)。考虑到所谓“up-or-out”(不升即走)体制的残酷性,尚未成为教授的教师很可能被迫去营造与决定他们命运的终身教授的私人关系。所有这些“人情”关系,在评聘和晋升副教授和教授的时候会变本加厉地发挥作用,而张教授大力宣扬的新体制对此同样无能为力。
不过张教授会说,新的体制有巨大的竞争压力,会迫使院系领导较少考虑人情,而且会间接劝阻那些较低水平的学者,使他们因为害怕竞争而退出市场。首先就第二个理由来说,即使在所有学者都能对自己有准确的自我评价的情况下(对学术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绝不是想当然的假设),也只有当学术竞争完全依照学术逻辑的条件下,这些学术水平较低的人才会主动退出市场。否则,市场“竞争”得越激烈,结果就会变得越不确定,一个愿意毕生致力学术的学者反而越有可能回避这样的是非之地,而选择可以安心做学问的地方。那些认为真正杰出的人就不会惧怕竞争的观点恐怕将学术研究的逻辑想得太简单了。即使不考虑学术评价中牵涉的复杂因素(比如在哈佛大学商学院,申请终身教职的人一般都有机会要求系里某些成员不参与评审推荐委员会的活动,理由可以是该人不足以评价自己的学术活动,或对自己抱有种族或性别方面的偏见),也只有当竞争完全依据学术逻辑进行时,一个优秀的教授候选人才可能在竞争中战胜一个水平低劣的候选人。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一流大学除了严格把关确保获得终身教职的教师的水平外,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评审,以避免对学者自主确定的学术研究计划的干扰。这些恰恰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充分尊重学术逻辑,充分认识到无限制的竞争可能给学术带来的危害,并力图提供有效的机制来保护学术的自主性。
那么,改革草案设计的体制是否会鼓励体制中的人们更多采用学术逻辑呢?张教授认为是这样的,在谈及有限次申报制度的优点时,张教授认为,过去的机制使院系领导过多地考虑基于人情的照顾或资历等,而新的体制则在这方面具有优点:“事实上,这样的规定对院系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如果一个优秀的人评不上,领导还可以用‘明年保证你上’的办法安慰他,但在新办法下,他不可能用这样的办法解决问题,一次的不公正就可能导致一个优秀人才的流失,优秀的人才不可能被长期压制。这是up-or-out(不升则走)制度的一个重要优点”。
不过,正象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张教授本人也承认即使在新的体制下,院系领导仍然很难避免来自人情方面的压力(“不是学校不相信院系领导的品质,但学校有理由担心,院系领导顶不住压力”)。换句话说,张教授清楚,院系领导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意愿,在没有真正的大学竞争体系和简明有效的学术评价体制下,院系领导会被迫屈从于各种非学术的压力,而所谓“竞争”的“赌注”越高,就会越吸引或迫使那些学术能力较低的人投身到“学术游说”的活动中,使院系领导面临更大的压力。在所谓的“新方法”下,或许院系领导很难用拖延来保住一个优秀人才,但他们会发现更难面对那些缺乏学术热情、却极具学术“活动”热情的人的压力。
据说,改革草案之所以先动教学人员,而暂时放过在校内受到更广泛批评的后勤行政管理等领域,就是因为后者阻挠改革的力量非常大,而希望借助教学人员的改革来推动行政人员的改革(张教授的“说明”隐晦地透露了这一意图,参见九。至于张教授提供的其他有关推迟改革更易于采用企业逻辑来改革的后勤人事制度的理由,不免荒谬,恐怕并非他的真实想法。毕竟,后勤人员的“服务态度”问题并非仅限于“水平”不够的教授,对张教授认为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学生,他们的“态度”更差)。不过,张教授虽然洞察了后勤领域存在的这种情况,但却似乎忘了,同样的“改革”逻辑在教学人员内部也存在。结果正象讨价还价能力极强的后勤人员迫使学校的改革设计者屈从他们的逻辑一样,未来在教学人员中,具有这种较强讨价还价能力、而非真正学术能力的教师,也同样会让院系领导屈从他们的压力。从教学改革与行政改革的次序选择上,我们有充分理由预见,那些更能阻挠而不是促进学术进步的人,很可能是最有力量在北大这次改革过程中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手段来施加各种压力,从而影响所谓“新方法”最终形态的人。没有真正考虑学术逻辑的新体制,只不过给这些人提供了进一步左右这个缺乏有效运作机制的方案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新方法”复杂的制度和激烈但却缺乏自主学术标准的竞争,将给那些擅长学术活动和讨价还价的教师以更大的用武之地。
正是看到了“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的内在困难,张教授才诉诸国外大学很少采取的所谓“末尾淘汰制”。张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威胁“把整个‘店’炸掉”,从而“保证了现有的教员有巨大的压力招聘更优秀的新教员,因为新进的教员水平越高,原来的教授的地位越稳,或者说,新进的教员水平越低,现有的教授工作越没有安全”。不过,这样的设想大概很难操作。如果连评价教授的客观标准都没有,又由什么权威机构来判定一个学科是否处于全国的前十名呢?即使在美国,比如商学院的排名,每年就有十余种,但没有一家是一样的,任何一家的排名也每年都在变化。有些学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纪报道》的排名中可能属于前5名,到了另一家,比如《华尔街日报》或《商务周刊》的排名,就可能在10名开外。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拥有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已经基本试行张教授新体制的优秀院系,再加上经济学院,共三家机构,但在教育部进行的高等院校重点学科的评比上却大败而归(在重点学科数上,排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和复旦大学之后,与辽宁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和武汉大学并列第五)。这样的学术评价大概不能抹煞北大经济学真正的学术地位,但却多少可以告诉我们学科的“末尾淘汰制”的可行程度。而且,这种整个学科的“末尾淘汰制”的威胁往往太模糊,太遥远,很不现实,很难象每次出现教授空缺的激烈斗争一样真正构成对院系领导或现有教授行为的有效激励。甚至张教授自己都承认这样的体制其实没有多少现实激励作用,而最后还是要回到原有的方法上:“退一步,即使你不担心你的院系被解散(因为它太大了,无人敢解散),学校也不可能对优秀人才流失严重的院系熟视无睹”。可惜“学校干预”这样的方法,不过是又回到了旧体制的逻辑。难道在现在的体制下,学校就会“对优秀人才流失严重的院系熟视无睹”吗?
其实,简单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张教授之所以在设计改革草案时,采用了“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和学科的“末尾淘汰”两套并行的激励体制来代替美国一般名牌大学采用的更简单的终身教职体制,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多少看到这两个体制实际上都很难真正按他的设想发挥作用。如果“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真的象张教授宣传的那么“见效”,以北大现有的学术声望和垄断性的资源分配优势,根本不会有什么大的学科长期落在国内10名之外。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本身就意味着很可能美国式的“聘任制和分级流动制”在中国与其说会鼓励一个学校留住热爱学术的优秀人才,不如说会使这些人才在更为频繁激烈的学术竞争中受到损害,最后被排挤出这个根本不尊重学术逻辑的名利场。问题是,如果一个学科真的采用了张教授设计的改革方案而在学术声望上出现大幅跌落,我们究竟该惩罚这个学科的领导乃至所有教学人员,还是这样一个失败方案的设计者呢?
因此,简单地说,张教授设计的所谓改革机制,其实不过是提高了旧的运作机制中竞争的风险,但却根本没有办法创造新的机制。以前当不上教授,可能只是不能带博士生,分不上房子,收入少一些,但至少你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来默默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而现在却是失业,剥夺从事继续学术研究的机会。所以张教授才会小心翼翼地在他设计的方案对“对院系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公正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惜,我们知道,旧的体制同样有类似的要求,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做到。除非找到把“要求”变成“现实”的真正符合学术规律的有效机制,否则,这些“理想”大概都不能代替可预见的现实,更算不上是“新方法”的优点。相反,它们只能表明,北大付出巨大代价得到的只不过是旧体制变本加厉的回归罢了。而且这种旧体制的翻版,由于“竞争”环境更恶劣,连旧体制相对较宽松的环境这一优点都丧失了。换句话说,张教授设计的草案在表面上和教育发达国家的体制相似,但因为缺乏各种真正有效的学术机制,整个体制的运转仍将主要依靠旧的逻辑,而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新方法”就不得不拼凑具有不同运作逻辑的美国体制:先是终身教职加上短期合同,再在独特的终身教职体制上加上学科的“末尾淘汰制”,然后还要加上“名额与质量双重控制”,为了解决后者带来的问题,又要根据不同学科制定所谓“动态平衡编制”。在这种依照旧逻辑运作的“新体制”中,每个新加入的体制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结果就需要设计更复杂的体制来解决,而更复杂的体制,由于还是依靠旧的逻辑运作,结果只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讨价还价、幕后活动和非学术竞争,这样,更激烈的竞争将更快地淘汰那些愿意遵循学术自身逻辑进行研究的教师。
而且,我们有充分理由预见,如果采取上述这些规定,那么在“新体制”下,各院系与学校的讨价还价活动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向教学科研的各个方面扩展。除了破格晋升,延长某些杰出人才的合同这样的问题外,举凡对编制名额的争取,不同院系的晋升标准,副教授长期职位的授予以及如何处置长期业绩不佳的院系(如果可能的话),都会在学校和各院系之间出现长期激烈的讨价还价活动。这与张教授设计新体制以减少院系内外的讨价还价活动的整体希望大相径庭(参见四,五)。
五,未来的教授从哪里来?
因此,在国内建立真正的大学竞争环境和广泛公认的学术评价机制之前,北大校内外的学者并不会因为采纳了所谓的“新体制”,就会自动依照新的逻辑来“竞争”和“流动”。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国内缺乏真正的大学竞争环境和有效评价机制的影响,海外的人才实际上就不受国内体制缺陷的限制。换句话说,尽管草案的设计者希望这些大学竞争环境会在未来逐步得以建立,但毕竟在一个类似欧洲情况的,私立大学缺乏有效影响的教育体制下,草案设计者梦想的美国化的“竞争和流动”体制如何真正出现,如何在中国学术界内部建立独立有效的评价机制,都超出了设计者能够设计的范围。不过,在草案设计者的心目中,即使这些机制付之阙如,他们的改革草案仍然有机会成功,那就是把北大嫁接在美国的体制上。制度嫁接成为制度移植思路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个意义上,张教授设计的北京大学人事体制改革草案实际上不过是吸引归国人才的方案。用张教授本人的话说就是,“改革将使北大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七)。
不过,这些人才不仅要从海外回来,而且因为国内体制的状况和“新方法”严酷的竞争环境(国内缺乏客观的评价机制,终身教职仅限于正教授并且受名额限制),很可能在北京大学获得终身教职要比在美国花费更长的时间,也要付出更多的非学术努力。因此,至少在拿到终身教职之前,这些人,如果不希望也变成学术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的话,也只有通过继续在海外杂志上发文章并利用海外的评价机制来确定自己的学术地位,从而获得晋升。当然,另一个更理想的行动策略是争取在海外某个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然后直接来北大申请教授职务,这样大概是风险最低,收益最大的行动策略了。这样看来,北大未来的教授可能在获得长期职务前,潜在的学术受众都是海外尤其是美国学术界,不论他研究的是致癌基因,多媒体文字识别技术,中国政治体制,还是汉语佛教和《诗经》。这样,或许北大在SCI上发表的文章会大大增加,但是否北大能够因此成为世界一流,却不一定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是否美国的中国研究足以成为中国自己大学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样板。毕竟有许多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国内学者从事这些方面研究的学者往往不象其他地区研究的本国学者那样受到重视。比如从事日本学研究的美国学者非常尊重日本本土的学者,每年都要前往日本取经,注意日本学者工作的新动向。这大概足以证明了日本大学在世界上的地位。而近年来,随着所谓与国际接轨的进行,中国国内许多领域的学术地位不升反降。在没有遵循美国标准来评价中国学术的时代,象哥伦比亚大学常务副校长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这样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美国学者还要到中国拜钱穆先生为师,以求指点一二,而且在多年之后撰写的著作中也不忘感谢那些指导他的中国老师。不过,要按今天的制度,恐怕钱穆先生这样连大学博士文凭都没有的小学老师,要先想办法请狄百瑞先生来做评审才行。而且钱先生当年在“落后”的制度下同样培养了十分优秀的学生。当年出资协助钱穆先生办学的哈佛大学方面都承认,“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之上多矣”(参见钱穆《师友杂忆》“新亚书院(四)”一章)。
不过,既然方案的设计者坚持要按美国的标准来衡量学术水平,坚持认为即便在传统中国学术的领域,海外学者也应该成为我们大学的评价标准(参见张教授网络答问)。这里,我们只考虑一个问题,在新的制度下,是否会实现张教授的理想,即北大最优秀的本科生,会选择留在北大读博士,而不是去国外读博士。毕竟按照张教授自己的说法,“仅仅满足于培养最优秀的本科生,我们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研究型大学”(七)。
从现有嫁接在美国体制上的制度设想来看,一个愿意致力于学术并希望终身为中国学术做贡献的人,越早离开中国到美国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越好,因为这样他会更容易适应美国学术界的要求,学会用美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问题,从而也更容易为美国学术界所接纳,发表文章和申请到研究经费,从而取得足够的学术声望。换句话说,既然在张教授设计的体制中,被美国学术界接纳,也就自然会有机会将来在北大成为教授,找到“长期职位”,那么我们看不出来,一个学生为什么还要冒向下流动的危险在北大读学位。而且,由于缺乏海外读学位的经验,这些学生在未来采取的海外评审等方面也会普遍处于劣势,他们会自然在高级职位的激烈竞争过程中被淘汰出局。在这样的体制激励下,北大大概永远也没有可能成为哈佛大学,倒是有希望保留哈佛大学研究院在全球录取本科生人数最多的大学这个荣誉。不过按照张教授自己的标准,拥有这样荣誉的北大注定不是第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不过是美国一流大学的预科班罢了。
六,北大能否靠“接轨”成为“一流大学”?
不过,有人或许会说,尽管北大只会接纳已经被美国学术界承认的学者做教师,但北大仍然会吸引许多国内无缘出国的优秀学生,而这些受到留美,甚至已经美国化的学者训练的学生,也会慢慢占领国内的所有大学,北大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就是在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之间“接轨”的道路。一旦中国大学都能和美国学术界接轨,北大就不再是嫁接到美国体制上了,而是通过自己的嫁接将整个中国学术界美国化或者说“世界化”了。方法很简单,就是从海外招聘一流学者,然后教出学生,占领国内的研究型大学(“未来中国教员市场的基本格局是一个分层结构:一流大学淘汰下来的被二流大学接收,二流大学淘汰下来的被三流大学接收”,八;“如果中国最好的100所研究型大学里有20%的教员是北大博士毕业的,并且他们又是各学校的学科骨干,我们就是中国大学当然的龙头老大”,六)。
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是否中国学术能否通过“美国化”从而“世界化”,也暂时不去关心美国高等教育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深层原因,我们只需要问一句,即使北大彻底采取了哈佛大学的体制,北大就能象哈佛大学一样成为世界一流吗?
根据张教授的说法,改革草案中推荐的方法“是国外大学的典型做法,无论这些大学是一流的,还是三流的”。换句话说,采用这种体制的,不仅有一流大学,同样也有三流大学。因此,即使北大采纳了张教授设计的体制,甚至即使这种体制能够按照张教授盼望的那样运作,北大也并不必然就成为世界一流,她同样可能成为一所三流大学。因为即便采纳了张教授设计的方案,未来决定北大命运的,也不只是体制本身,而是在这种美国化的体制中的竞争优势。
那么,什么是美国化体制中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呢?根据张教授对这种体制的描述,就只可能是“钱”。换句话说,北大能否在自己极力想加入的美国体制中成为一流大学,根据“新方法”的逻辑,就要看北大是否能有机会招聘到世界一流的学者。而根据张教授描述的学术市场情况,决定何为一流学者的,主要是他的市场价码。因此,北大是否能成为一流大学,就变成了北大在整体上,而不仅仅是一个光华管理学院,能否支付相当于美国一流大学的教授薪水。我想,对这个问题恐怕不需要再具体举什么复杂的统计数字来回答吧。北大现在实行的九级教师待遇制度,最高的一级教授年津贴为5万元人民币,约6000美元。即使算上各种其他收入,恐怕也难以超过1万美元。这笔钱,大概比在美国读博士生的平均奖学金还要低。凭这个收入去美国大使馆签证,恐怕连签证官都会怀疑你是否会归国效力。而美国大学,根据AAUP(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2003年的最新统计,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研究性大学,占教员总数的38.9%的教授平均工资是97,910美元,副教授占26.2%,平均工资为67,043美元,而占教师总数24.8%的助理教授的工资也有57,131美元。如果算上其它类型的教员,总体的平均水平达到73,997美元,再加上其他方面的福利,要超过9万美元。而张教授津津乐道的哈佛大学是美国大学支付教授最高的学府,教授的平均薪水达到约15万美元,在哈佛当副教授和助理教授虽然淘汰率或者风险高,但收入几乎达到外校教授的水平,分别是近9万美元和近8万美元,这些还没有考虑哈佛大学为教职员提供的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各项福利(美国一流大学教师的福利往往包括从医疗保险、住房津贴直到孩子大学学费等各种美国人生活中开销非常大的项目)。即使在美国高等教育体制最底层的两年制社区大学(大致相当于我们的大专)的教师平均工资也要51,619美元。即便我们扣除货币实际购买力方面的差异,太平洋两岸的教师收入也基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换句话说,以北大现在支付教师的薪金水平,恐怕连社区大学的助理教授都聘不到,更不用说什么世界一流学者。
另外,就办学经费而言,北大在985计划第一期3年共获得18个亿人民币的额外资助,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将来不见得会增加,甚至张教授自己都不能保证北大会持续得到同样水平的资助(一)。而即便这笔巨额资助,平均每年也不过区区7500万美元,加上北大的其他日常办学经费,总数估计不到1亿4千万美元。设计改革草案并鼓吹学习哈佛成为世界一流的教授们大概不会不知道哈佛大学每年的经费情况吧?根据哈佛大学最新公布的财政报告,2002财政年度,哈佛大学办学的总经费为近24亿美元,而其中来自联邦政府的资助不到17%,更多是来自经营哈佛大学高达213亿美元的总资产的收益(32%)和来自学生方面的收入(22%)。而且,在同一财政年度,哈佛大学获得的捐助总数达到4亿7千万美元,而这居然都不是当年美国最高的,最高的南加州大学得到了5亿8千5百万美元,而排名第10的杜克大学也有超过2亿6千万美元的捐助。就研究经费而言,排名在美国前10名大学之外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年得到的联邦科研资助超过7亿9千万美元,总数则超过9亿美元,哈佛大学的总科研经费也在3亿美元以上(2001财政年度)。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以往起点上的差别,不考虑美国大学可以在全国共享的资源,仅就现在北大资助的水平,如果嫁接到美国的体制上,不用说一流大学,恐怕连二流大学都没有机会。北京大学目前办学经费的总体水平,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大概只相当于美国优秀大学40年前的水平(比如哥伦比亚大学1960年代的经费在1亿2千万美元左右)。1992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因为经费紧张,试图取消了十几个系或专业,还准备终止与逾百名终身教授的职务,结果引起了法律和学术上的巨大争议。而当时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经费是1亿7千万美元左右。
那么,在现有的教师收入状况和大学经费水平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有可能建立一流大学呢?答案是肯定的。问题是这就要逐渐摸索比照搬哈佛大学体制更耐心但却可能更有效的办法。其实,即使在美国的大学竞争体制下,也不是所有的大学都采用哈佛这种高淘汰率的明星教授制度,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大学,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美国名牌一流大学,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制度。原因很简单,以“挖角”为基础的明星教授制度,是需要巨额经费支撑的。即使象哈佛大学这样学校资金远远超出美国其他学校的巨型大学,她的校长也觉得这样的明星教授制度对学校财政具有巨大压力。如果他想用这样的办法来建设整个大学,要维持这样的大学运转下去,恐怕最后他就要把哈佛大学Fogg博物馆的名画都卖掉,然后象某些中国大学一样向全世界出售哈佛的文凭(参见Derek Bok在2003年的新书Universities in the Marketplace的前言中讲述自己关于哈佛大学商业化的噩梦)。甚至早在1930年代,27岁出任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30岁就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美国教育界传奇人物Robert Maynard Hutchins就曾在他的《论美国高等教育》一书中对这种严重依赖巨额财政花费的办学方针大加针砭,“仅从财政的观点看,大学也许接受了捐赠之后会变得更糟。而从教育或科学的观点看,它可能会变得不够平衡,充满混乱。依赖捐赠者一时的兴致意味着没有人能够预见过了一年大学的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我并不是说大学不需要钱,也没有说大学不应该努力去争取钱。我的意思只是大学应该有一套教育政策,然后想办法为它找到资金,而不是让财政上的偶然变故来决定他们的教育政策”(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我们同样也希望,北京大学的改革方案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难以保障的巨额政府拨款上,而是建立真正尊重学术逻辑的体制,培养有助于学术发展的氛围。
那么,美国其他一流大学建立一流院系的方法主要是什么呢?与哈佛大学相比,之所以这些大学大部分都采取从副教授开始授予终身教职的制度,就在于这些大学利用这样的体制来兼顾竞争性评价与培养两个方面。换句话说,这些大学不只是去别的学校去挖已经成名的教授,而是同时立足在本校培养符合终身教职学术标准的教师。比较优秀的教师经过6到7年的考察,往往就能获得终身教职。获得终身教职之前的试用期(probationary period),不仅是学校考察教师的时间,同样也是培养教师成长,使教师与该学校的研究传统逐渐相互适应的阶段。因此,这些一流学校的一些院系往往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自己独特的研究传统,而不受一时学术时尚的摆布。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当经济的建设一流大学的方法。既然不能在薪酬上与资金雄厚的超级大学竞争,许多学校就力争在学术氛围,职务稳定性等方面建立自己的优势。利用这种方法,许多与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上颇有差距的公立大学同样有机会跻身一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其中的代表,该校近些年一直排名全美前列,在一些权威排名中名列前十。其他一些公立大学,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密歇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以及近年来学术声望迅速上升的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都是拥有许多顶尖学科的名校(参考Hugh Davis Graham和Nancy Diamond著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而且,哈佛大学能够招聘到一流学者,首先是因为存在一流的学者,而这些学者往往是在哈佛之外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真正决定美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不是寥寥几所拥有巨额资金从而可以四处挖“角”的超级大学,而是许多能够培养优秀人才的一流大学,甚至州立大学。尽管这些大学未必总能保住那些社会名声很高、社会活动频繁的明星教授,但是它们往往拥有一大批认同美国大学的教育传统,不仅能够独立从事前沿的学术研究,而且对教书育人极为认真负责的教授。这些才是美国高等教育长盛不衰的根源。相反,倒有不少美国高等教育的有识人士,批评明星教授尽管能有助于提高学校名声、吸引捐款、争取资助,但往往对实质提高教学水平助益不大,而且助长了片面追求商业化从而争聘明星的风气。哈佛大学政治学(Government)系著名教授Harvey Mansfield在接受全美学者协会的胡克(Sidney Hook)奖的演讲时就说,“哈佛是今天美国大学的领头羊,但这不是因为哈佛拥有最好的教师或者最精明的管理者,而是因为哈佛拥有最好的学生”(”How Harvard compromised its virtues”, The Chronicle Review, Vol.49, No.24)。听起来,口吻和张教授对北大学生讲演时没什么差别,可惜哈佛的教授知道哈佛的问题在哪里,知道应该如何采用学术的逻辑来使哈佛变得更卓越,而北大有些教授却学而不得其法,怕是越“改”离“一流”越远。
七,什么是“世界一流”?
张教授在回答有关北大吸引力的问题时,曾经承认新草案的机制需要两个假设,“北大有足够的吸引力,市场上有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可供北大挑选”(七)。张教授只回答了第一个假设,但却不能说服我们市场上有足够多的优秀人才可供北大挑选。事实上,连张教授自己也承认,在国内北大可以算上一流。只不过这样的“一流”不足以让人满意。如果这个问题在整个国内学术界都存在,那么北大的困境不过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整体问题。张教授设计的草案的重点是筛选人才。但中国学术界的真正问题却是缺乏可供挑选的优秀人才,而且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不着眼于创造健康的学术环境培养人才,更不珍惜已有的人才,而只是满足于用一些适合新闻炒作的方法来“吸引人才”。但如果没有人才,“吸引”的条件再好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北大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带头力量,应该更多着眼于培养中国学术界的人才。因为,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作为一所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北大很难采用哈佛大学的“明星制”来成为所谓的“世界一流”,但她实际上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通过培养学术氛围等其他手段来立足国内培养那些真正热爱学术的学者,并利用这种经济条件之外的优势来吸引海外真正关心中国学术事业的学者。而在这方面,核心的问题是如何逐渐形成一个和谐宽松,有利于学术成长的环境。
如果说,一个有利于学术成长的环境需要尊重学术的逻辑,那么如何将北大带向真正的一流大学,就要弄清楚对北大现有不同学科而言,究竟什么样的学术方向,才是真正迈向“世界一流”的方向。
比如,北大的理工科院系,在现有的资金条件下,是否能够凭现有的实验条件进入世界一流。究竟哪些领域有这样的机会,哪些领域没有。如果有些学科在二三十年内都没有可能进入美国标准的所谓“世界一流”,这些学科是否应该停办,还是应该为更长远的学术发展进行扎实的基础性学术积累。
象管理学院和法学院这样的职业学校(professional school),如果按照某些美国排名标准来计算毕业生的工作起薪的话,大概除非中国经济水平超过美国,永远没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但如果评价对各自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力的话,怕是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和法学院也不能相比。如果是这样,它们的“世界一流”又应该如何衡量呢?我们的“职业教育”是否有助于培养这些学院的毕业生肩负影响中国未来生活的重大责任呢?除了日益向美国看齐的专业技术知识训练外(在这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是否在中国的法学院,也应该教授英美的习惯法,而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体系呢?),我们的法学院是否也能象许多美国一流大学的法学院一样,通过切实的公民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在受这次改革冲击最大的人文科学领域,恐怕大部分不带偏见的人都会承认其中许多学科是北大在世界上具有绝对领先地位的学术领域,甚至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北大成为“世界一流”的主要机会。尽管外国学者确实也在研究“我们的文化和历史”,甚至有不少颇有建树的学者,但是否在中国历史,中国语文和中国哲学方面,海外学者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能够甚至应该成为评价中国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呢?如果北大进一步的体制改革,是要在制度上建立这些学科在学术评价体系上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依附,我们将来要聘请汉语都说不好的人(这一点稍微熟悉海外汉学状况的人就知道并非个别或者例外)来国立北京大学来担任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终身教授,那么是否这些学科还有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呢?事实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美国主流学界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任何在美国有过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些领域几乎从未超出地区研究的范围,在美国也很少吸引到第一流的学者,更不用说对学科外的其他研究领域的影响了。尽管这些年,中国研究日益受到美国学界的重视,但仍然无法与欧洲研究,更不用说美国对自己的研究相提并论。其方法和理论大多是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少真正具有前沿意义。以美国学术界的边缘学科来规范中国大学中最具学术底蕴和研究传统,也是对中国人的政治经济生活与文化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部分,这是否是与建设一流大学的努力背道而驰呢?有这样想法的人告诉我他是孔子的信徒,秉承的是儒家的精神,如果不是个恶意的玩笑,我只能承认我们大学的人文教育确实太薄弱,甚至终身教授都分不清孔子与樊迟,孟子与梁惠王的差别,把“上下交征利”也当成了儒家的学说。
最后,在社会科学领域,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或许张教授设计的方案遇到的“硬件”困难较少,这些领域很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实验室,而且因为许多美国大学中都有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或是政治学者,也很容易在美国招聘到相关领域的教师。但是否一个在美国学术界的格局中主要从事地区研究的经验学者能够在北大在相关领域引导具有理论性的全局研究,却并不是容易回答的简单问题。毕竟即使在美国非常成功的华裔社会科学学者,也较少是在学科的一般理论和主流领域中取得成果,而更多是在定量方法或是地区研究方面有一定造诣。一般来说,只具有这些领域的知识背景的学者往往缺乏将社会科学的经验取向与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创新的能力。而且由于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的相对优势和在人文背景方面的相对劣势,大部分留美学人更多是受美国定量研究方法的影响,往往对人文学科内在的学术逻辑不能理解,甚至不够尊重,这在这次改革草案的设计和讨论就表现得非常清楚。这样不仅不能利用北大在传统文科方面的优势以促进社会科学系统思想和基础理论的形成,而且也客观上妨碍传统文科借鉴社会科学的新方法,对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成长都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而没有人文学科的支撑,没有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良性互动,北京大学的文科很难达到真正的一流水平。
总而言之,如果立足招聘海外人才回国来建设中国的一流大学。即使我们假定北大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并借助其他方面的吸引力,那么从港台学生开始留学至今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哈佛大学除了在东亚研究领域,又聘用过多少华裔教授呢?在整个美国学界,又有多少华裔教授真正在各个领域是从事前沿性的研究呢?如果我们在美国都无法招聘到足够的一流人才,我们岂不是永远也不能建立所谓的“世界一流”了吗?何况在招聘这些海外学者时,正如张教授意识到的,北大的吸引力并不是“钱”,而是悠久的人文传统,在中国文化、思想和政治上占据的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但所有这些,在新的改革草案中,都是想方设法加以革除的阻碍改革的落后力量。但试问如果这个嫁接在美国体制上的所谓“竞争和流动”新方案真的成功地消除了这些“落后力量”的话,又有几个真正优秀的海外人才愿意回到这个绝对三流的冒牌美国大学中呢?毕竟,没有独立自主的中国学术,丧失了精神上的祖国,海外的优秀学者们又有什么必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呢?
八,结语:学术自主与中国学术的未来
张教授的改革草案的核心是所谓tenure-track制度。不管张教授设计的方案是否真的是美国大学广泛采用的终身教职制度,学习研究这项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制度本身并没有错,但要清楚这项制度背后的逻辑,才能学到门径,否则就象张教授在网上回答问题时所说的,“根本不知道国际的学术规则,不知道国际一流的大学是这样运作的”。自从1915年,终身教职制度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就一直是这个制度的重要特征。而AAUP(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之所以引入这个制度,并非只是出于某些既得利益者的需要,而是旨在借助终身教职的工作保障或者说经济保障来确保学术自由。这一点在AAUP在1940年发布、至今仍为美国各高校普遍遵循的《有关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之原则的声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中就明确加以确认(参见Richard Chait ed. The Questions of Tenure。《声明》全文在许多地方可以找到,例如Richard T. De George著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
根据这份声明,“高等教育的各项体制致力于共同福祉(common good),而不是促进个别教师或整个高等教育制度的利益。而共同福祉则依赖于对真理的自由探求及其自由阐发。学术自由对于实现这些目的来说具有本质意义,而且既适用于教学,也适用于科研。科研自由对于推进真理具有根本意义。而教学方面的学术自由则在根本上有助于保护教师教书的权利和学生的自由学习。与这些权利相应,学术自由也有其相应职责。终身教职作为一项手段,特别有助于实现以下目标:(1)教学研究以及校外活动的自由;和(2)充分的经济保障,从而使这项职业足以吸引有才能的男女。因此,自由和经济保障对于一项旨在履行其对学生和社会的义务的制度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1960-70年代因为政治原因,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制度曾引起很大争议,但经过十几年的讨论,终身教职与学术自由的密切关系再次得到确认。AAUP在1971年成立的高等教育终身学术职务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n Academic Tenure in Higher Education)最终对这个问题提交的报告指出:“终身学术职位之所以得到认可,就是因为它在维持学术自由和教师质量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是美国高等教育教员人事体制的根本组成部分”。终身教职制度与学术自由的紧密关联是公认的,正如评论者所说,“无论是历史上的作者,还是当代的作者,都力主学术自由是终身教职最重要的目标”(参见William Mallon, Tenure on Trial,页20)。
那么,究竟什么是终身教职制度保护的学术自由?中国人一想到学术自由,就先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保障教师的学术观点不受外来政治力量的干预(参见二,以及张教授在网上回答有关学术自由与竞争的关系方面的问题)。但我们不能混淆了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实际上,研究终身教职制度的学者指出,这一制度根源于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制度。对蔡元培时期北京大学办校方针影响颇大的洪堡,早在1815年的备忘录中,就已经强调了学术自由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终身教职强调的学术自由或者更准确说学术自主,具有相当宽泛的意义,它不仅指获得终身教职的大学教授在研究、发表和教学等诸多学术环节上不受学校行政管理等方面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强调学术活动有自身的逻辑,学术逻辑不应该屈从于经济、政治等外在的逻辑。建立终身教职制度的大学的目的是在现代社会中捍卫学术自主性的堡垒。没有这种学术自主性,张教授所谓新观念或者新价值的创造根本无从谈起。而在今天,正象哈佛大学前校长Bok指出的,坚持学术价值,拒绝让大学听命于经济逻辑,就是坚持学术自由(参见Universities in Marketplace)。
事实上,这种学术自由也正是80多年前蔡元培先生改革北大的最重要的意图,当年蔡先生因五四运动之故暂时辞去校长,曾发表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思想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先生当初来北大,就立志革除北大的腐败。而这种腐败的集中反映就是当时的学校中充满了官商两种习气,却无真正的学术气氛,先生有关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者的论述正是针对这两种陋习所发:“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有不少专门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先生此后更是屡次强调用学问之道克服北大教师学生中的官商两种腐败习气,而且在有关“大学改制”的辩论中,特别指出这是他改革北大的指导思想,是他以文科兼法商二科的缘由:“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几,不相侔也。鄙人初意以学为基本,术为枝干,不可不求其相应……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这种以学术逻辑主导大学的“学术自主”,就是蔡先生所谓“自由大学”主张的核心,是蔡先生一贯坚持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方针”:“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而要坚持这一点,蔡先生以为一定要反对大学的急功近利(参考“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并借德国大学发展的历史指出,“盖兴学之初,目光短浅,重实用而轻学理”,而北京大学经过改革,能够与德国之柏林大学相比,就在于以学理发展文理两科(“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而“大学学生,本为研究学问而来,不要误认这学问机关,为职业教育机关”(“北大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我们绝不把北大仅仅看作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倾向”)。而今天,我们唯有反对急功近利的思想,才能坚持北大的“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才能实现蔡先生本人当年的殷切希望:“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萃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现在,张维迎教授的支持者呼吁要仿效蔡元培先生推动北京大学的改革(例如周其仁教授2003年6月29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关于“教育国有化和教授终身制”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我们希望这样的改革能够继承蔡先生当年的精神,建设一所真正能够引导中国学术发展的大学,以学术自主的态度克服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对学术的侵袭,培养有利于学术自主成长的环境,促进学术自身逻辑在北京大学的体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避免重蹈北大官商两种腐败。但可惜的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次改革草案充满了经济的逻辑,也不乏对改革涉及的各方利益的政治考量,但似乎唯一缺乏的是对真正学术规律的尊重,对真正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学术逻辑的思考。在网上回答问题时,张教授经常指责北大的老师“太封闭”,不了解国际统一的学术规则。但一个根本不尊重中国学术发展逻辑,用市场竞争代替学术成长,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嫁接美国体制的改革方案,是否真正尊重了国际的学术规则呢?张教授乐意援引象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姑且不论这些地方的大学体制是否都和张教授设计的体制一样,但至少这些地方都既没有张教授希望的世界一流大学,也没有完全独立自主的学术世界。相反,欧洲大学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但却始终没有简单地追随美国的制度,并始终能够保持它们在许多研究领域中的领导地位。
即便谈到美国自身,如果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成型的时候,那些著名大学的校长一心只想模仿欧洲大学,恐怕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毕竟,美国早期高等教育在学习当时的先进欧洲国家时,并没有一味学习德国,或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文化强国——法国,而是通过综合洪堡式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和英国式的自由教育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两种体制,逐渐发展形成了美国式的高等教育模式,能够结合自主的科学研究,健全的公民教育和教学相长的“高深学习”(higher learning)。在此前,美国也曾有很长时间依赖从西欧输入思想与文化,但美国之所以创办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这些都是今天北大人事体制改革方案希望实现的所谓“研究型大学”的方向),就是为了培养自己的思想家,使美国大学成为美国科学的摇篮。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就是美国思想和文化寻找自己“灵魂”的历史(参见John Brubacher和Willis Rudy所著的权威的美国高等教育史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urth Edition.特别见页438以下论美国高等教育与众不同的特征)。
今天美国高等教育体制能够成为北大改革草案一心仿效的对象,就是因为当年美国没有象个没有主见的尾随者,把德国或别的欧洲国家看作自己体制的唯一标准。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来看,美国的教育之所以是“世界一流的”,就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想亦步亦趋地跟在“世界”后面,而是始终努力寻找适于自己教育理想和国家情况的教育体制。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难道不值得深思一下吗?中国改革已经不只20年了,作为曾经参与其中的学者竟仍然认为改革只需要拿过来别人的制度,甚至连制度都不用拿过来,只需要嫁接在别人的制度上,就可能成功。这岂不成了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经验”的改革道路的最大嘲讽吗?
与终身教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学术自主,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学术界的成长需要摸索自身的逻辑,建立起适合自己情况的学术体制。而没有灵魂的“制度移植”,甚至更加偷懒和缺乏信心的“制度嫁接”,都在根本上与“学术自主”背道而驰。而在根本上不顾学术自主,甚至背离学术自主的“tenure-track”制度,恐怕不会给中国学术带来什么光明的未来,尽管它可以盗用人家教育的美好形象来为自己宣传,但那是虚假华丽的修辞,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在中国实行终身教职制度,那么首先要找到这项制度真正的“精神“,否则就象我们已经分析的那样,必然变成新瓶装旧酒的把戏。而在中国,终身教职制度是否可行,即使可行,如何实行,这些都需要我们花更长的时间来探讨和摸索。张教授在“说明”中曾经强调,“招聘和晋升是大学教授除科研和教学外最重要的工作,多花点时间是值得的,是事半功倍的事情”。既然值得在招聘和晋升上多花点时间,那么设计一个尊重中国学术逻辑的招聘晋升体制就更值得多花点时间。因为,虽然某些对北大和中国学术毫无感情的媒体可以宣称,无论成功与否,这份改革方案都可以作为管理学院未来研究的案例,但对于北大自身来说,一旦错了,却可能不仅丧失历史再也不会给予的机会,甚至更糟糕的是,摧毁了北大师生自蔡元培先生以来一直勉力维持的中国学术传统。张教授在“说明”中曾经反驳批评者说,“一个想有大成就的人,难道连一点耐心也没有吗?如果没有一点耐心,我们怎么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呢?”我相信所有真正关心北大的老师学生都希望改革的设计者和执行者能够真的多一点耐心。希望张教授们真的记得孔夫子的话:“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据“世纪中国”网站、《书城》2003年第8期)
作者简介:李猛,1971年生人。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北大社会学系任教5年,曾获北大第六届“十佳教师”称号,现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