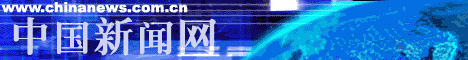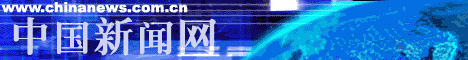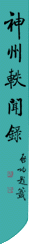在北京成千上万的养鸟者当中,最气派的莫过于养鹰了。论个头儿,一尺多高;论分量,二三斤重;论形态,文翮鳞次、砺吻钩爪。如此雄健威武的庞然猛禽架在胳膊上,怎能不引人注目,又如何不气派?
鹰,亦称苍鹰。从《诗经·大雅·大明》中的“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一语看来,远自中古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然把鹰这种猛禽看做是是奋扬威武的象征了。
隋朝开皇年间,设置骠骑将军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大业3年(公元607年)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为鹰扬将军,车骑将军为鹰击郎将。足见当年的统治者在武将中极力提倡鹰的奋扬威武精神。
关于大批驯鹰使其成为狩猎工具的史料记载,亦始见于《隋书·炀帝纪·大业四年》:“征天下鹰师悉集东京,至者万余人。”唐代沿袭了前朝饲鹰遗风,专设鹰坊,由闲厩使(官名,圣历中置)管辖。由于朝庭与民间养鹰之风日盛,因此以鹰为题材的唐诗亦层出不穷。例如杜甫的“万里寒空只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力赞了鹰的形美与善飞;柳宗元的“凛然空翻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声情并茂地状出了鹰的敏捷与磅礴气势;而耿炜的“举翅云天近,回眸燕雀稀”则描绘出雄鹰凌空搏风,杀气森森的威慑之貌;而苏东坡:“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那驾鹰出猎的气势,又是何等的奋发、昂扬。
剽悍而又极善狩猎的满族人进关后,帝王与贝勒们每年冬天都要穿着罕德罕(满语:鹿皮)的马褂,外罩罕德罕的坎肩,架着鹰牵着狗,下南苑海子(皇家狩猎苑囿)举行声势浩大的围猎活动。上行下效,天子脚下的庶民亦渐渐以养鹰猎兔为乐事。
养鹰猎兔虽有逸趣,但“熬鹰”却往往使人精疲力尽。刚捕的幼鹰,野性很大,必须昼夜看宁,勿使其得分秒睡眠;此外尚须禁食,仅喂其白菜水。如此不食不眠一个月左右,俟其体重由三斤降至七八两,再补以肉,使之恢复原来的体重;稍事训练即成得心应手之猎鹰了。
猎兔的情景是扣人心弦的,主人站在荒野的高处,除掉鹰帽、爪套及爪链,鹰便环视四周,跃跃欲试。主人的几名助手四散于方圆数百亩的荒草丛塚中,以修长的枣木杠儿左右搜寻,徐徐前进,忽听枯草刷刷一响,随后便有一只野兔霍然窜逃;那躲在远处的猎鹰早已瞋目而视,猛然腾空而起,恰似一道闪电凌空掠过,及至俯冲下来,可怜那野兔立即鲜血迸溅,气绝身亡矣。无怪乎唐诗人章考标有诗赞鹰曰:“穿云自怪身如电,杀兔谁知吻胜刀。”而王摩洁《观猎》中“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则更是传诵千古的名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