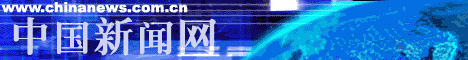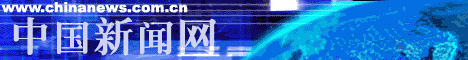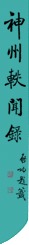被老北京人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名叫黄才贵(后改名黄德胜),字治安。因其身体魁梧,且出身行伍,故得“大兵黄”之绰号,而其本名反而少为人知。
“大兵黄”少年时曾拜董海川(清中叶人,八卦掌名家)第一代传人学习八卦掌和八卦门器械。20岁以后,先后在张曜、马玉昆、蒋桂题、张勋等军阀部下当兵,并于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参加甲午战役。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大兵黄”从张勋的“辫子军”中退役,因生活没有着落,遂落魄天桥卖艺。初期,尚练些武艺,后来转变成专门针对军阀权贵人物进行嬉笑怒骂,每骂完一阵,便卖一回药糖。
30年代时,北京的一些报刊均刊登过“大兵黄”的照片,其形象为:头戴青缎帽头儿,花白胡须胸前飘洒,上身穿绛紫色马褂,下身着黑绒套裤,足蹬青缎面千层底双脸儿鞋,手持一个油光红润的葫芦和一挂香木捻珠。如此不伦不类的打扮及其跳脚狂言的特殊表演,遂使这位艺人的兴趣,而且为各报的新闻记者甚至当局所瞩目,因而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大兵黄”骂军阀,如同说书一般,每段自成一回,淋漓尽致地揭露各个军阀的内幕与丑剧,虽不免有些夸张或不实之词,但总的来说与事实基本相符。
譬如骂北洋奉系军阀张宗昌,对他出身土匪以及先后投靠直系军阀冯国璋、奉系军阀张作霖等情况说得头头是道,然后以“他妈的小舅子”这句口头禅将话一转,骂张宗昌有33个姨太太,是“望乡台上摘牡丹——不知死的鬼”!张宗昌在山东任军务督办时,有一年庆祝寿辰,宴请麾下师长、旅长,席间命一最得宠的爱妾品箫,曲罢满座皆叹服。爱妾说:“奴家吹箫不如我翁公吹得好。”翁公者,乃张宗昌之父,原是吹鼓手。张宗昌闻听此言,恼羞成怒,以为扬其家丑,当夜就将爱妾枪毙了。“大兵黄”绘声绘色地说至此处时,往往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将其手中的白蜡杆子(练武的器械)往地下拍的一摔,大骂一声:“他妈的小舅子,张宗昌活畜类!”众人听了,咋舌的咋舌,缩脖的缩脖,点头的点头,在深感快慰和钦佩“大兵黄”的同时,也不免为他捏着一把汗。
“大兵黄”骂北洋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更是痛快淋漓,入木三分。曹母乃麻脸、缠足,有一年赴天津看曹锟,坐马车逛街,无意中将小脚儿露了出来,当时曹锟拜见母亲说:“有件事禀告母亲,孩儿乃堂堂大总统,希望你今后出门别再把脚伸出来。给我留点儿面子。”翌日,曹母又外出,故意露其金莲。是夜,曹锟复上常拜见,未及开口,母先曰:“有道: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似你这般忤逆子,不配做我儿子,更不配当总统,你当总统,百姓遭殃!从今以后我不认你这个儿子!”
“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烧杀奸淫,野蛮残暴,无恶不作。此时的“大兵黄”亦敢大骂日本兵,将他耳闻目睹的日本军官兵种种罪恶行径骂得狗血喷头,因此而被外五区警署多次拘禁;但一俟释放,依然照骂不误,确实表现出一般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慨,客观上对激发大众的抗日情绪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凡是当年听过“大兵黄”骂人的老者,无不称道他是一个性情耿直而不畏死的硬汉子。这位奇特的天桥艺人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具有无穷的魔力。只要他斜背着满满的一口袋沙板糖(长方片形,内含薄荷),刚一露面,立即就被众人围拢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买他的药糖,不是为了解馋,而是要听他的“骂世”,以排解各自心中的忧烦。
“大兵黄”屡被官府扣押,他却全然不放在心上。每天开骂之前,他总说“我身上带着殃榜哪!”所谓“殃榜”,是旧时迷信之说。人死后要请阴阳先生将死者姓名、性别、年龄及其“出殃”(指灵魂脱离躯体)和“回殃”(谓灵魂回家探望)的时辰写在一张黄纸上,于入殓时焚化。“大兵黄”带殃榜之说,犹如武将抬棺而战,含有拼死之义。
记得文人金寄水,作过一首咏《大兵黄》的竹枝词,略谓“骂不绝声立广场,群皆瞩目大兵黄。官僚军阀从头数,博得游人笑断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