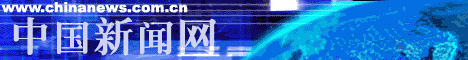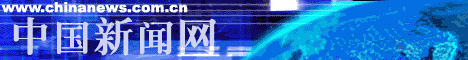几位朋友饮茶,聊起老舍先生的《茶馆》,称赞之余,免不了为他的撒手人寰更增几分哀叹。由此,老舍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又俘现在眼前。
我和老舍先生相识是在三十年代的北京,未见面之前,就听说他在北京读书时,不但功课出色,而且非常健谈。当时学校每周末有讲演会,虽是为了锻炼大家的口才,但几乎每次都被他独占鳌头。这充分表明了他具有演讲的天才。等至一接触,果然名不虚传,看上去似很严肃,一谈起话来,却幽默风趣,常常引得人捧腹大笑。这在后来,也成了他创作上的独特风格。
当时,他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就是梁实秋先生,也很健谈,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总是海阔天空,聊个没完。这个恢谐地说东,那个幽默地道西,这个笑谑地说南,那个便风趣地话北。抬不完的杠,顶不完的牛,常使人笑得肚子疼。大家常议论说,如果他俩说一段相声,一定是一对好搭档。不想这个想法于十几年后居然成了现实。
那是抗战时期,我辗转到了重庆,住在风景如画的北碚文化区的一座小山上,正巧老舍和梁实秋也住在那里。其时的老舍先生已是誉满海内外的大作家了,在重庆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梁实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两人时相过从,见面仍是那么恢谐、笑谑、使人愉快。
1944年秋天,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庆,校长余上沅先生邀请了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出度。会上大家各献节目,热闹非凡。有人乘兴建议请老舍先生和梁实秋先生说一段相声,顿时群起响应,掌声如雷。他俩面带笑容,相互一瞥,就这眼神的一传递,就把大家逗乐了。于是俩人同时起身,各从怀里抽出一把破旧摺扇,似乎早已准备好了的,摇摇摆摆登上台去。两人恭恭敬敬向大家鞠了三个躬,然后,一个面容郑重严肃,一个笑得直不起腰来,就像传染一样,马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接着,老舍先生用扇子向大家一指,全场立即安静下来。他们两人你敲敲我的肩,我戳戳你的头,用道地的北京话说起了相声。虽然两人事先并未商量,完全是即兴发挥,但配合默契,天衣无缝。一会儿这个一本正经,一会儿那个笑容可掬,信手拈来都是笑料,表演得既熟练,又精彩,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令人拍案叫绝。全场笑声鼎沸,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的人笑得流出了眼泪。
1949年,老舍先生自美国飞回大陆,陆续写了不少剧作;梁实秋先生则去了台湾。而今,他们都已先后作古,空留下一段文坛佳话。
(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