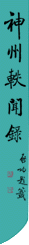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那些年代中,北京因政府南迁,再加受到当时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所以市面比较冷清;能够用以点缀的,就是一些中学和大学了。尤其是大学,国立的“三大”、“二专”,即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艺专和体专,每月南京教育部有一笔固定款项汇京。清华也是国立,但用的是“庚款”,是另外一笔;燕京、辅仁、中法、协和医学院,都是教会办的,款由教会拨。另外还有私立的中国大学、民国大学、华北大学、京华美专等。一些著名的大学,经费充足,讲师、教授的工薪都比较高,因而就生活优裕,颇为大家所羡慕了。
《罗曼罗兰传》一书的译者鲍文蔚先生,曾留学法国,回国后三十年代初在中法大学作教授,另外又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收入在300元左右。当时物价便宜,面粉只要3元左右一袋(22公斤),300元收入就很可观了。当时鲍先生住家共有两个小院,8间北屋,有盥洗间,有浴缸,有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书房、客厅四壁书架上有由法国带回来的千种的精美书籍。这在当时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其生活之优裕可以想见。
有些留学国外的教授还娶了外国夫人。有的外国夫人自自也是教授,他们住的往往是有花园的房子,生活水准之高,是可以想像的。
三十年代初,北京国立大学还有“部聘教授”的名称,即聘书由教育部发,如刘半农、钱玄同、徐志摩几位先生都是,薪金高达500元。可惜好景不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七七”事变之后,教授生活每况愈下,一落千丈了。
在1937年至1945年北京沦陷期间,“有四大贱物”之说,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因为别的东西都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东西,却迟迟未曾涨价,因而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为“贱物”,则是一样的。
教授的生活水准,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在谢刚主先生给徐一土先生《一士类稿》写的《序言》中有几句道:“在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象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点点心。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饼和面条,就当晚饭。”这就是由战前的吃馆子,到沦陷初期只吃点点心,再到买烧饼当饭。不过这是家中人口少,有余力的。在最艰难的吃混合面(用玉米茎、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年月里,家中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热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是要煞费苦心,甚至是很难办到的。
冯成钧老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为同学们上课,同学们就到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的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得在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扯扯拉拉,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与夫人分着吸。现在还健在的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伯老先生,到学校时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到沙滩上课。就如前文说的鲍文蔚先生吧,这时在沙滩文学院作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庖人、女佣等,只好由鲍师母自己做饭。先生也无力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