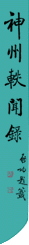大凡是老北京人,该不会不记得厂甸儿吧。
那是个传统的大集市。清代《帝京岁时纪胜》里,就有“每于新正月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的话。逛厂甸儿,曾是北京人过年的一件大事儿。
一出和平门,顶打眼的是路旁的两溜儿暖棚,里头静雅得很,展销着国画、书法、挑山、横披、册页等等。棚角儿还摆着红木高几,碧桃、腊梅、迎春、水仙悄悄儿地散发着清香。顺南新华街往前,路两边儿就是卖吃食和玩意儿的了。论吃食,从铜钱儿大的豆渣儿糕,到5尺长的大糖葫芦儿;从顶着胭脂点儿的江米爱窝窝,到香油和面,层层起酥的荤素油酥火烧;乃至灌肠、豆汁儿、粳米粥、八宝饭、煎春卷儿、炸松肉、串成佛珠状的大山里红——举凡北京风味儿小吃、干鲜特产,全有。玩儿的呢,那贴着金字红签儿,抖起来音响激越的单双空竹,由一个个彩纸风轮儿带动小锤儿,敲着一面面小鼓儿的各式风车儿,已经够人眼花的了;而那些大小“沙燕儿”,拖着彩绸尾巴的“龙睛”,活眼珠儿、活关节儿的“蜈蚣”,则展现了京派风筝的多姿多彩。面对这些别具风格的爱物儿,无论童叟,谁不神往呢?至于“面人儿汤”当场献艺,在半个核桃壳儿里捏的《十八罗汉斗悟空》,“葡萄常”亮出的绝活——那颤着枝儿,甩着蔓儿,挂着白霜儿的“玫瑰香”、“马奶子”,就更为人们惊叹了。
从十字路口往右,进西琉璃厂。荣宝斋的水印笺纸,德古斋的金石片,吸引着学者文人。往左呢,进东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糕,戴月轩的狼毫笔,久已驰名了。而路北那座火神庙,则是个珠宝古玩市场,几进院落,都平地搭起两丈高的蓝布罩棚,虽在白昼,却如夜市。明灯下,那些紫檀架、琉璃柜,宝气珠光,土花铜绿,夺目极了。说到那棚幕,似也另有妙用。除了借着大瓦数的电灯,显示其珠宝的光华,古玩的文彩之外,或许还大有助于遮美玉的瑕纹,掩珍玩的残迹,甚至鱼目混珠,也都自得其便吧。难怪清人咏厂甸儿的打油诗里头,就有“古董般般的是新”的句子。
说到南新华街与东西琉璃厂相交的十字路口,以及路口近旁的海王村公园么,虽是厂甸儿的中山地区,可惜,那儿却象是市面儿上常见的各色商品的抽样儿综合陈列,反倒没什么厂甸儿自个儿的神气了。
厂甸儿是很有吸引力的。清人《厂甸记》曾这样记载着:“平时空旷,人迹罕军;而正月则倾城士女,如荼如云,车载手挽,络绎于道。”听一位住在火神庙院儿的老管理员说,抗战之后,厂甸儿已是“残灯末庙”景象了,可游客每日仍过万。半月累计,约20万人次。而当时北京人口,也只百万上下。
论游人,且不说那些显宦宿绅,名儒大贾;鲁迅寓京期间,就很爱逛厂甸儿,在有日记可查的13个春节里,是每年必逛的,1913年,开市的半月间,竟去了7回;13年累计起来共达40多次。先生从那里购回的文物、古籍、儿童玩具,乃至日用杂品,都被一一载入了日记当中。这些日常细事,似也都成了当今鲁迅研究者们所瞩目留心的史料了。至于谭鑫培曾在这拍摄了北京梨园史上第一张剧照《定军山》,梅兰芳曾在这儿搜集古画儿,揣摩新编剧目的头饰服彩,也为许多老北京所乐道,至今都不失为艺坛佳话。
游人中也难免有不速之客。据说,民国初年曾震动京津的大盗燕子李三,有个同伙叫段云鹏的,就到这销过脏。被盗者是慈禧同族、叶赫那拉氏后裔。就在火神庙一个珠宝摊子的玻璃盒里,失主认出了家传珠宝,一串光润绝伦的珍珠,寻着了破案线索。这该是那个时代遗留给厂甸的一点儿痕迹了吧。
话说回来,厂甸儿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除了别的因素,这儿雅俗共赏,老幼皆宜,富裕些的,清寒些的都可有所获,怕也起了相当作用。请想,一粒明珠,一方古砚,自非显贵莫得,非专家莫辨;可一碟儿糖豌豆,一盏走马灯,虽是平民童稚,也不难到手。人们可以掂量着自个儿的财力,依了各人的喜好,或快其颐杂,或饱其眼福,或遂其雅兴,何乐而不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