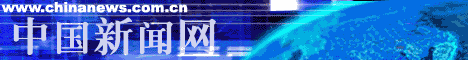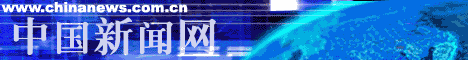章大牛在那次差点要了他命的“体检”中死里逃生,已经8年了。那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迄今惟一的一次“体检”。但是直到今天,他仍不清楚那次“体检”的真相。
这位55岁的安徽枞阳县农民记得,1995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上面来人”叫他到镇卫生院去“体检”。章大牛的妻子周真梅说,他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就去了,因为据称“体检”是给农民服务的,“有病给你治病还不要钱”。这对平时“没钱买药就望着”,有钱买药也得等到实在喘得受不了时才吃一片的章大牛夫妇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
章大牛夫妇有四个儿子。他们按要求带着两个儿子去“体检”。因为没钱坐车,他们步行十多里地,赶到镇卫生院,得到一顿免费午餐后,下午开始检查。他们回忆,同时做检查的还有来自其他村的二三十人。
不过,在章大牛所在的村民组30来户人家中,他们是惟一被喊去参加“体检”的。周说,因为都晓得章大牛从20几岁就患哮喘病,已经多年了。想不到的是,她说,“检查就差点检死了。”
出事之前,他们被量了体温,抽了血。然后检查者让章大牛张开嘴,向他嘴里喷了一种“雾一样”的东西,让他说“啊”。章大牛夫妇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吸入这种化学药品干什么用,可能引起什么风险。
那东西“是装在一个塑料瓶子里,像打灭蚊剂一样的,”周回忆说。“‘啊’了三、四下他就上不来气了,像死了一样。”时隔8年,周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在场的医生都怕了,赶紧抢救,“挂水(输液)”、“灌氧气”。做检查的医生没有一个是当地的,说话口音就不一样。但是章大牛夫妻俩都说不上来他们是哪里来的。
周说,为抢救章大牛,给了他们不到200元,“别的人就没有给”。章大牛一直到后半夜“气才接上来”。这之后,就没人再管他了。第二天,无人过问的夫妻俩离开了医院,自己找了辆便车回家。
抢救章大牛的时候,有个大夫答应以后给他们寄药来,但是他们“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药”,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体检”的结果。同为文盲的两夫妻说,无论“体检”之前还是之后,他们从来没有看到或听说过“知情同意书”,更没有在这样的文书上签过名或按过手印。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血样“贡献”给了什么机构。
哈佛项目
枞阳县另一个村子的村医张复年倒是知道那次“体检”是“给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基因研究”做的,虽然他说不上项目的名称。52岁的张自1969年开始当村医,已经30多年。他说,“当时要我们通知农民去‘检查身体’,看是什么原因引起哮喘的。”他肯定,当时“讲了要治疗,后来没有。我们问参加体检的人员,搞检查的人是哪儿的都不知道。”
1995年早稻出苗前后的一天,张陪着参加“体检”的村民到了县防疫站,“移交”名单之后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体检”的过程。没有人告诉他或者任何受检农民,检查有哪些程序,也没有告诉他们“体检”的结果。他和这些农民都没有看到或听说过“知情同意书”,更不知道血样会被送往美国。“这个事在1995年以后就没人提起了,”他说。“不了了之了。”
但是,哈佛群体遗传学研究计划的负责人、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徐希平和他的同事自1995年以来发表的好几篇论文却表明,枞阳县是哈佛大学一系列人类基因研究项目采集基因样本的现场之一,其中一项就是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和“著名生物药品公司”千年制药公司共同资助的哮喘病基因研究项目,其首席研究员就是徐希平。
1999年12月一期《美国呼吸及重症保健医学杂志》发表了徐希平与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学教授、哈佛医学院医学教授兼其教学医院布里汉女子医院主任医生斯考特·韦斯(Scott.T.Weiss)等合写的论文《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肺功能家庭聚集》。他们在论文中声称,他们“在中国安庆进行了一项大规模遗传流行病学研究,检查环境和遗传学因素对哮喘病的影响。……调查是从1994年7月1日到1998年1月26日进行的。……对每一个参加调查的家庭都发了一封信,解释这项调查。从8个县(枞阳、怀宁、潜山、桐城、太湖、望江、宿松和岳西)招募了1161个有哮喘病患者的指标家庭的成员”。这8个县都属于安庆市。文后的一个注脚表明,这项研究的资金分别是NIH麾下的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和千年制药公司提供的。
奇怪的更正
在这篇论文发表两年之后,该杂志在2002年的166卷刊登了徐希平和韦斯为他们所发表的总共7篇论文所做的类似更正,称他们在中国的有关呼吸系统的遗传学研究是在取得当地中国IRB(即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后,“于1995年2月开始的”,“布里汉女子医院IRB的批准是1995年9月收到的”。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更正呢?1999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一些专家对这个项目提出的疑问,开始了一场为时三年的调查。针对联邦政府提出的问题,徐希平于1999年12月3日致函当时哈佛大学负责此事的人体研究事务办公室负责人考斯基(GregKoski),称被质疑的研究是“中国研究人员”在“1994年7月获得安庆医学伦理委员会”的IRB批准后开始的“试点研究”。徐在信中说,他1994年10月向布里汉女子医院人体研究委员会提交人体研究申请,“1995年9月最终获得批准”,所以“正式的合作研究1995年10月才开始”。
按照这封信的意思,错误是在与哈佛的“正式合作研究”开始之前,中方研究人员在“试点研究”时犯的,与哈佛无关。美国调查者接受了这个解释。但是,且不说没有哈佛的招牌及其雇员带来的资金,中方当时是否可能启动这样大规模的基因样本采集,就是哈佛自己的文件档案,也在证明他们早在1994年,就至少已默许了这个项目开始实施。布里汉女子医院医学系主任尤金·布朗瓦尔德(EugeneBraunwald)1994年11月15日签署的核准《哮喘病分子遗传流行病学研究》项目“在研究中使用人体方案”,详细描述了将在枞阳和怀宁进行哮喘病基因研究的程序。该医院的人体研究委员会则在1994年11月23日致函徐希平,通知他,在“1994年11月15日”的会上,“本委员会投票批准了”这个方案,只是要加以修改,包括“在(知情同意)表中删去所有提到布里汉女子医院的地方,加上合适的机构或名称”。徐将改动意见于1995年1月6日上报给委员会。千年制药的业务总管斯蒂文·霍孜曼(StevenH.Holtzman)也在1999年11月12日向美国联邦政府调查人员证明,千年制药与布里汉女子医院在1994年就达成一项协议,资助徐希平博士主持的哮喘病分子遗传研究项目,“包括从中国采集DNA样本”。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自己的刊物《哈佛公共卫生评论》和千年制药的新闻公报,都在1995年9月以前公开报道过这个项目的进展情况。
如果“正式的合作研究1995年10月才开始”,哈佛大学的有关研究机构为什么没有及时制止在这之前就以其名义进行的这些活动,并允许公开报道?如今发现这些活动违规,又以所谓“正式的合作研究”当时还没有开始来推卸哈佛大学有关机构应负的责任,这难道是一个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对待错误的应有的科学态度吗?
至于徐希平向美国联邦政府调查机构所说的“安庆医学伦理委员会”的“IRB批准”,截止到2003年9月14日,在安庆市卫生局的网页上遍查不到这个机构。经电话向安庆市卫生局查询,一位工作人员说,“从来没听说过”。安庆市114电话查号台也不知道这个机构,而安庆医学会接电话的一位先生肯定,安庆市从来没有过这么一个机构。即使在众多中国人对医学伦理还十分陌生的1994年,安庆市果真有这样一个机构批准了这项研究,哈佛大学依然不能逃避它的责任--“课题首席专家”是它的人,而文件中的规定都没有得到遵守。
哈佛的承诺
一位美国专家认为,哈佛有关机构花这么大的力气,把1995年9月以前为千年公司在中国采集基因资料的工作说成是中国方面的“试点研究”,可能是有意洗清自己违反联邦政府规定的责任,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监管,对私营公司进行的人体研究,特别是国际研究,要比对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松得多。而哮喘病项目最初就是由私营机构千年公司资助的。”
然而,这种做法却不符合哈佛有关机构承诺要遵守的伦理原则。它们在申请研究经费时,向美国政府保证,在所有涉及人体作为对象的研究项目中,都遵循同样的原则,“无论对象是谁,也无论支持经费来自哪里”“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这些原则要求以人体为对象的研究项目,必须先取得IRB批准以及每个研究对象签名的知情同意书。知情同意的内容必须包括,让每一个研究对象“充分了解研究的目的、方法、资金的来源、任何可能的利益冲突、研究者所属的机构、预期的受益、潜在的风险和研究可能引起的不适”,知道自己“有权拒绝参加实验或在实验过程中有权随时收回对参加实验的同意而不遭到报复”。同时,国际上早已形成共识,并以文件规定,“知情同意是一个过程”,是获得同意的过程,而不是用书面、签字等形式获得文书的过程。
但是在实际中,美国的调查者强调的却是书面的文书。只要徐希平提供了所谓中国地方IRB的批准文书和大量有签名的所谓“知情同意书”,他们就不再深究了。对于中国农民是否真正在“体检”的当时签署过这些文件,是否了解知情同意应当涵盖的所有内容,他们却没有认真核实。农民章大牛和村医张复年及其他很多被抽过血的安徽农民,连徐希平提交给美国有关方面的“知情同意书”样本都没有看到过,更不要说其他了。事实上,有关研究目的和程序的详细说明,徐希平和他的哈佛同事都给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调查者,而没有给这些农民。
谁是受益者
这些项目的真正受益者是谁?
1996年,徐希平在向NIH申请资助这项哮喘病基因研究的预算论证中这样写道:“美国有1200多万哮喘病人,……美国每年花在治疗哮喘病方面的费用估计在60亿美元。”在哮喘病和慢性阻碍性肺病这类气管疾病中,要害的问题是具有很强的基因基础的气管感应和肺功能水平。他建议在中国安徽进行“基因筛选”,因为那里人口“众多,是同种,大多数人没有看过病”。
哈佛与千年公司在1994年12月达成的合作协议规定,“在中国安徽表型500个家庭(400个哮喘病家庭和100个非哮喘病家庭),并把从这500个家庭获取的DNA送往千年公司,以通过匿名标记做基因组搜索,寻找哮喘病基因……千年公司对他们所发现的任何基因享有惟一的专利权。”
需要说明的是,哮喘病仅仅是哈佛在中国进行的十多个人类基因研究项目当中的一个,这些项目都涉及采集中国农民的血样做基因筛选,以求找出与哮喘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等一系列疾病有关的遗传联系。其中好几项都是先由千年制药资助,然后才获得NIH资助的。
千年制药对哈佛哮喘病项目的资助不过300万美元。在它于1995年7月宣布自己能获得安徽的哮喘病基因5个月之后,瑞典制药业巨头Astra公司即给千年公司提供5330万美元在呼吸系统疾病领域进行研发。而千年公司对来自安徽的肥胖症和糖尿病基因的掌握,则吸引了另一世界制药业巨头Hoffmann-LaRoche7000万美元的投资。千年制药的股票价格,从1995年5月上市之初的每股4美元,飙升到2000年6月的每股100多美元。其若干高层人员通过股市交易,每人净赚1000万美元以上。
至于徐希平,中国证券网报道说,2002年底在完成注册登记的安徽康诚药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总资产为999万元,其“35%的权益由自然人徐希平教授持有”。另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厅网站的消息,2003年6月,由徐希平牵头的8位海外华人“投资在宁夏留学人员创业园组建银川生物医药研究院,预计投资两千万元。”提到姓名的几个人都参与了哈佛在安徽的基因项目。
所有这一切,被采集血样的安徽农民都不知道。他们除了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贡献”了血样,什么也没有得到,就连徐希平在给NIH的资助申请书中承诺的“免费医学建议”,他们也没有得到。
没有伤害吗
在一些学者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哈佛这些项目提出质疑之后,美国联邦政府于1999年开始对这些项目进行调查。但是,在调查由新成立的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负责之后,担任其首任主任的不是别人,正是原在哈佛领导对哮喘病研究的内部调查的考斯基。从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获得的有关文件表明,考斯基当时就向联邦政府提出,没有必要对在中国的哮喘病基因研究做进一步的纠偏行动。而在联邦政府结束对该医院的调查之前不久,考斯基即于2002年11月宣布辞去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首任主任的职务,回到哈佛任职。
联邦政府的调查确实发现哈佛这些项目在生命伦理方面存在“广泛而严重的违规”。但是,他们仅仅对哈佛的研究者及其合作者提出质疑,而且基本上依赖于徐希平及其哈佛同事对质疑的回应。人体研究保护办公室没有派自己的工作人员到中国现场做过调查,美方调查者没有访问过章大牛这样的农民,也没有找任何对这些项目有不同意见的中国人士了解情况。
哈佛自己派人到中国调查的结论成了美国政府结束对哈佛项目调查的依据。记者曾通过电子邮件问今年4月来中国调查的哈佛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主任兼布里汉女子医院医生特洛严·布伦南(TroyenBrennan):他是否讲中文?能否用中文与安徽农民直接交流?如果不能,他的翻译是谁?他在中国的访问会见是谁安排的?他去过哪些采样现场?他是如何肯定知情同意书是研究对象在研究进行的当时签署的?他的调查有多大的独立性?但是,这些问题都被转给了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负责对外宣传的罗宾·赫曼(RobinHerman),医生兼律师的布伦南本人则没有回答。赫曼只转来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在美国政府调查结束后,于5月30日发表的一份正式声明,与记者提的问题毫不相干。
尽管章大牛们对哈佛项目一无所知,但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声明却说,(中国农民)“参加者给出了自愿的知情同意”。该院院长柏利·布鲁姆(BarryR.Bloom)强调说,“哈佛谋求在其所有的工作中确保对人体研究对象最高水准的保护”,“没有一个参加者受到了伤害,没有发生一起有意违反人体研究对象程序的事故”。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Summers)2002年5月还曾经在北京大学承认哈佛在中国进行的基因项目“非常糟糕”,但是现在却为“调查表明我们的研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而庆幸。
且不论章大牛的遭遇是否是“伤害”,是否代表了“对人体研究对象最高水准的保护”,难道对中国农民知情权的漠视,就不是“伤害”?难道违背生命伦理的准则,不是问题?
美国联邦政府接受了哈佛对违规的“纠正行动”。然而,作为被哈佛违规伤害的主体,广大安徽农民却根本不知道哈佛大学究竟怎样纠正了错误。他们的知情权依然没有得到尊重。
疾病缠身的农民章大牛还在盼望着答应给他的药。而村医张复年对哈佛的项目,心中仍然存着疑问,希望能对它们“追根究底”,“让我们都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来源:《瞭望》周刊2003年第38期,记者:熊蕾、汪延、文赤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