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社主办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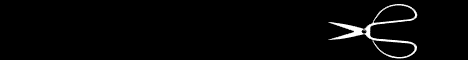 |
| |
中国首批维和民警在东帝汶 2001年3月6日 16:14 口述:徐志达 采访:邱四维 2000年1月,龙年春节前夕,在别人合家团圆的时候,徐志达带领14名中国民警启程,去了陌生的、仍未摆脱骚乱的国度--东帝汶。 2001年1月23日,中国传统的除夕夜,是徐志达他们留在东帝汶的最后一晚。我国派往东帝汶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维和民警68人齐聚一堂。第一批要走了,第三批刚到,辞旧迎新,难舍难分。包饺子、喝老酒、高唱《送战友》,所有的人都流下了热泪。大年初一早上5点,徐志达他们离开东帝汶首都帝力,前往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年初二,乘飞机抵达悉尼,当晚乘上中国国航的航班,年初三终于回到北京。 元宵节的第二天,我有幸采访了徐志达。 徐志达: 1966年生,1988年毕业于中国警官大学;任职于公安部警卫局,少校军衔。2000年1月率14名中国民警赴东帝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民警参加维和,徐志达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 维和民警是这样选拔和培训的 1998年,中国开始酝酿培训和派遣维和民警。1999年3月,公安部决定从六个省市进行初选,推选40名候选民警到公安部参加特别考试,选拔第一批学员。 维和警察的人员选拔条件相当苛刻,须得通过"五关":第一是英语关,要求每个候选人的英语水平必须在非专业六级、专业四级以上,听、说能力俱佳;第二是政审关;第三是业务关;第四是形象关,对每个候选人的五官、身材、体态和仪表都有很高的要求;第五是年龄关,缺乏经验的年轻警察不适合,经验丰富但体力不够的大龄警察也不合格,最佳的人选是年富力强、有七年以上警龄的。 按照这一标准层层选拔,全国各地警察部门初选出了40名优秀警官参加考试。考试的标准按联合国要求,科目主要是英语、国际法和汽车驾驶,最后由专家进行心理稳定性测试。经综合测评,最后只录取了20人,成为中国首批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受训人员。 培训在解放军某学院进行,因为他们有军事维和的经验。培训科目除按联合国规定的课程外,还有一些军事观察员根据维和经验设立的课程。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这对中国民警来说,是个不小的问题。为了营造语言环境,学员从入校开始,无论是上课还是平时生活,一律都用英语,以强化英语听说能力。此外,熟练的驾驶技术是每个维和警察必备的技能。汽车驾驶训练有山地驾驶、越野驾驶、泥路水坑特殊条件下驾驶、单双边桥驾驶等。语言和驾驶两项基本功训练完成后,才是业务培训。 首先是生存训练,诸如在巡逻时发生意外如何处置,怎样才能脱险、求生等情况都要考虑到;其次是武器的识别,虽然维和人员都不配武器,但同样要熟练识别了解各种武器的性能、特点,以防不测;其三是学习掌握联合国工作的一些常识,维和警察常要与世界粮农组织、能源组织、卫生组织、难民署、红十字会等进行协调,怎么打交道,如何沟通都是必备的知识。 训练开始是在1999年5月,至7月结束。公安部领导参加了我们的毕业典礼。典礼上,我代表全体学员汇报:"已按联合国要求完成训练项目,进入待命状态。"训练结束后,学员回各单位待命。同时,公安部外事局通过外交部向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通报了情况,由他们通知联合国维和部:中国有20个民警通过培训达到了联合国要求,随时可以派往任务区。同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根据我们的外交需要,考虑向几个任务区提出了申请派遣维和民警。但由于培训学员只有20个,各任务区申请的数量不是很大,所以向东帝汶只申请了五个。 前往东帝汶前,我们都写了遗嘱 1999年8月30日晚,我们突然接到联合国电报,要求我们申请派遣的五人于9月4日到达东帝汶任务区在澳大利亚的培训基地。因为时间仓促,其他民警还在各省待命,出于办手续等考虑,就从北京籍的民警中选拔了五人,由我带队去。其中一名是公安部机关搞通讯的,其他三名都是北京市局的。联合国要求在9月1日给予答复,于是当晚我们就起草文件,发出电报。 因为没有维和经验,办理手续和购置装备肯定来不及,我们向联合国申请延期到8日。联合国给的装备清单就有几十项,于是向公安部申请调运装备。装备分被装和装备两种。被装包括到热带去的床、睡袋、衣物等,装备包括使用的工具、设备、警具等。最后我们还是在三天内把装备紧急调运到位,把护照签证也拿到手。那段时间我们从没有在夜里12点前离开过办公室。 也是在8月30日这天,东帝汶全民公决结果出来:45万选民中,高达78.5%的选民投票支持独立。但在投票结果揭晓的前一晚,反对东帝汶独立的亲印尼民兵已经察觉到情势不利,于是掀起一场暴乱。9月3日联合国工作人员从东帝汶撤离到澳大利亚。在原定出发日期前一天,也就是9月7日,我们接到联合国通知,任务推迟了。 联合国撤出东帝汶后,积极努力组织大规模的维和行动,需要各成员国继续增兵,也向中国政府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提出了增兵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外交部协商,决定进一步增派民警,从五名增派到10名,再从10名增派到15名。这样,第一批总共派出15名。那时每天从互联网上收集到的有关东帝汶的消息都是血淋淋的,东帝汶的天空被黑烟遮蔽,民兵放火烧毁建筑物,还针对支持独立的人士发起死亡攻击,用枪挑着人头在街上走,大街上到处都有死尸。 东帝汶任务区的危险,对我们即将前往的每个人都是一种压力。我专门回了趟老家,把8岁的儿子交给兄弟,请兄弟帮我照顾好儿子。跟父母也只说去印尼附近的一个岛屿,为联合国工作一年。让我真正感到压力的是,一起参加培训的四个战友,有的刚结婚,有的孩子很小,我带他们出去,如果谁有个长短,没法向他们的亲人交待。我们每个人都写了遗嘱,这样如果以后发生不测,也好处理善后事宜。 后来任务推迟了,又进一步增派人员,因为这次维和特点发生变化,联合国要代行临时政府的职责,民警要负责执法,所以要求我们携带武器。10月,我们又被紧急召集起来,到武警学院练习射击。最后,根据多年使用武器的经验,我们决定带中国生产的五四式手枪去。12月底,我们接到任务,联合国要求我们在2000年1月13日到达任务区。这时我们无论从装备上还是培训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没想到中国民警的素质这么高!" 2000年1月13日,我们第一批十人从北京出发,(第二批五人25日从北京出发),取道悉尼,于当地时间13日晚上9点到达联合国设在达尔文市的维和民警训练基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面临到达任务区的第一关:通过联合国的考试。因为中国民警是第一次参加维和考试,尽管准备很充分,还是有些紧张。在出发仪式上,公安部领导反复向我们交待:首次派出,要一炮打响,要不辱使命。 那天英语听力考的是一个案件题,分别由两个口音比较重的外国民警来读同一个案件,然后让回答十个问题,答对七个才算过关。由于口音较重,语言又是我们的弱项,所以大家都有些紧张。所幸在国内培训的基础扎实,全部都通过了考试。 联合国官员对我们的考试成绩比较满意,香港无线电视台跟踪我们采访的记者采访培训基地的官员时,他对我们的评价非常好:"没想到中国民警的素质这么高!"毕竟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一举一动都很受瞩目,达尔文当地一家报纸也对我们进行了采访,标题很大:"中国民警明日赴帝力",还配发了一大幅照片。 1月19日,我们离开培训基地前往东帝汶。当时正是雨季,帝力机场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水坑。我们的行李被维和部队的铲车铲起来,"哗"地一下扔到地上。没想到机场的条件都这么艰苦。联合国维和总部在帝力市中心,从机场到那里的公路还可以,但战乱刚过,作为首都的帝力也四处都是烧毁的房屋,街上除了联合国的车辆外很少有别的车辆,行人也很少,没有店铺,偶尔在路边看见当地居民,面部表情也都非常呆滞。看着这些经过战乱的痛苦后麻木的面孔,我们的心里感觉真是凄凉。 到总部办完check in(登记)手续后,联合国民警的人事官员和我们说了几件事:第一,分配每人的工作去向。第二,每人食宿全部自理,联合国只负责发给大家津贴。现在你们暂时没有住的地方,可以先到奥林匹克吧(联合国租用的一艘船)上去住,但住在船上,每天一半的津贴将被扣走。如果想节省点钱,必须自己租房子。第三,明天来报到上班。讲完三点,人事官员走了。我们一听,都愣了,刚到这里,上哪儿租房子去?住船上,光住宿就扣掉一半津贴,还怎么吃饭?但当天没办法,只好住在船上。 第二天报到上班,我被安排在下午巡逻。在船上吃饭时认识了一个律师,愿意租他家房子给我们,报到后我和另一个民警打车去租房子。出门就遇到两个帮派火并,看着当地人扛着大刀,还有打枪的,感觉还是比较危险。后来是分到监狱的同志在同事的帮助下租到了一套民房,我们在船上住了五天后就搬走了。 我们的生活:和罐头、烈日作伴 我们住的房子就和国内农村的平房一样,所谓的卫生间和厨房都是搭在外面简陋的棚子,住的地方也没有自来水,水要从水井里压。当地的水质经过化验有污染,不能饮用。联合国每天供应一瓶供饮用的矿泉水,洗澡洗衣只能用井里的水。当地治安比较乱,每天联合国的车接送我们上下班。 平时也没什么娱乐,在那里一年没看过电视。要看电视得自己弄卫星天线等接收设备。我们五个民警一起住。买菜是利用每月一天的休假,坐UN的免费飞机到达尔文买。由于没有保鲜条件,在达尔文采购的多是罐头,回来在当地买点蔬菜黄瓜吃。 刚到帝力时,整个帝力市只有一个华侨开的非常小的小卖铺,营业时都铁门紧锁,要买东西,敲门,店主看清来人不是坏人,才敢放进去。物价贵得不得了,一个小的烤面包机在国内也就几十块人民币,在那里要卖90美元,一根黄瓜也要卖一美元。经过战乱,没人种植粮食,许多当地人吃饭都靠联合国救济,所以蔬菜很少。 在东帝汶过了两个春节,也就是大家在一起聚一下餐,心里感觉不到任何春节的气氛--穿着背心满身流汗还过什么春节?!平时和国内联系不太方便,刚去时两个多月才能收到国内的信。当地只有帝力市能打手机。我们有两个同志被分配到欧库西飞地,(一块属于东帝汶,但三面被西帝汶包围、一面临海的地方)条件非常苦。因为飞地在动乱时受到的破坏最大,四面都被印尼包围着,后勤供给是个大问题。食品粮食都送不过去,商人重建的积极性也不高,没人到那里投资,他们刚去时根本没法通信,要住一个月才能回来休假。UN有卫星电话,但电话只能用于工作,我要与他们联系只有到联络中心给他们发一个很短的消息,能不能收到还难说。我们平时用煤油炉做饭,他们那里做饭只能用柴火,而且只有吃自己带去的罐头,还因为水土不服,拉肚子。通讯各方面都受孤立,联合国在那里的人也少,一共有20多个警察。他们在那里工作一个月后,回来看到他们体重降了很多,大家看了心里很不好受。但没办法,总要有人去干这工作。我曾经想过派人和他们换换,但他俩说:别人都坚持下去了,我们也坚持下去!我们在那里确实不好过,但别人来不也是一样受苦?而且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了,环境也熟悉了,别人来了还要重新适应环境,不是更苦吗?这样他们就在那里坚持工作了一年。 染上登革热,好几次我问自己会不会死 东帝汶的热带病,常常让人谈虎色变。当地比较厉害的两种疾病,一种是登革热,一种是疟疾。一位来自加纳的维和民警,就被疟疾夺去了生命。 东帝汶雨水多,蚊子多,染上疟疾的机会也多。我们每天晚饭后都要吃一片叫做Doxcig的预防疟疾的药片,尽管副作用比较大,但还是得吃。白天上班前,还要在身体暴露处涂上防蚊子叮咬的药水。尽管炎热,我们出去时尽量穿长衣长裤。 热带蚊虫很厉害,蛇和蝎子也多。我们不少人被蝎子咬过,幸运的是,都是毒性不太大的。来自上海的饶灏就遭了一劫。一天晚上,饶灏不知被什么虫子咬了一下脚踝,脚肿了起来,还突然发起了高烧,联合国卫生所的医生也不知所措。饶灏拿出了自带的云南白药敷在脚上,也无济于事。由于警官缺乏,饶灏硬挺着值夜班,一声没吭。不久,脚踝烂了,饶灏便脱去了军靴,穿双拖鞋执勤。就这样,脚踝烂了两个月才结疤。 登革热是热带的一种传染病,无药可治,大家都害怕得这种病。而我不到一个月就得了。一开始就是发烧,症状不明显。UN在当地有个临时建的卫生所,缺少必要的设备,医疗条件也差。我到卫生所看病,做血液测试不是疟疾,觉得可能是感冒,没事儿,开了些感冒药就走了。结果服了好几个剂量号称是全球最好的退烧药,烧都一直维持在40度左右退不下来。烧得每个关节每条肌肉都疼,像被撕裂了的感觉。连续高烧了一个星期,脸上和四肢都出现了紫色的斑,当时我心里已经知道可能是登革热了,但我没说,怕引起大家恐慌,后来同事一致认为我是登革热,就向国内作了汇报。国内很着急,部领导作了指示,马上回国治疗。当时我想:第一,我是队长,回国治疗会动摇军心;第二,反正这种病没有药治,回国无非营养好些,干脆不回去了。发高烧睡不着觉时,几次我问自己会不会死?一想到自己这么年轻,还有孩子在等着我,就说不能死,要挺住,一定要扛过去。 因为身体素质比较好,国内又通过外交手段积极为我创造治疗条件。后来又持续低烧一周后,病竟然就好了!还真扛过来了。 打这次生病后,我对危险不是特别恐惧了,我觉得无药可治的病都没死,以后就不容易死了。 工作:用实力、努力和魄力说话 刚到联合国工作,大家不了解中国民警素质如何,加上没有维和经验,所以都从基层巡逻干起。咱中国民警一般会外语的来自基层的不多,现在从基层做起,比较苦。但经过一段时间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对任务区比较熟悉了,语言关也克服了,工作起来逐渐得心应手,才能逐渐显露出来。我们有计算机通讯这方面的专家,联合国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就逐渐换了工作。 我是在巡逻两个月后受命组建科摩罗分局并出任局长的。帝力市警察局分为三个分局,科摩罗分局占整个帝力市案件的60%,帝力市又占整个东帝汶案件的50%以上,所以我这里占整个东帝汶案件的30%。应该说这个职位是块"硬骨头"。当时有几个职位可以选择,我想中国民警来时都在基层,如果显示不出实力来,对以后的派遣很不利,所以选了最硬的骨头啃。 当时房子都被烧了,到处一片废墟,组建时比较困难,光做人员、财务、装备等各方面的计划、报UN审批、由他们组织施工队施工就花了两个多月。第一期工程修好后,我们来自十多个国家的18个民警进驻开始工作。18个民警担负着打击整个东帝汶地区30%犯罪率的任务,困难可想而知,每天案子很多,有时夜里睡着觉就被叫起来出现场。后来随着人员逐渐到位,好一些。我走时有30多个民警,加上当地招募的警察,总共有四十五六个人。 刚建局时只有巡警没有刑侦队,所以打击犯罪非常困难。后来我申请建了一个刑侦队,把国内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经验应用到了这里。要求处理案件快,执法严。执法的力度加大了,特别是有了刑侦队之后,破案率、结案率都大大提高。 有几个大的案子印象比较深。我当巡警时碰到过一个大的案件:在联合国难民署附近一个村庄里两伙人打架,被打伤的人集结他的帮派扛着大刀回来,砍伤了很多村里人,还把村里的一个首领绑架了。当时警察局没抓人,只是把当地领导人拉到一起进行谈判,放了人质就算了。我被派到村里监视帮派,那些人扛着大刀就在警察面前耀武扬威。这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明显是刑事犯罪,是黑帮,怎么不用刑事手段来解决?我出任科摩罗分局局长后,这个村子正好在我管区内。因为知道以前的事,就派警察悄悄收集他们的情况。一天我正在办公,电台里又传来打架的消息。原来是两个家庭的孩子打架,一家就找了黑帮,把另一家砍伤了两个人,而且扬言如果报警就要把全家烧掉。我问清受害者是帮派干的,就马上立案了。我把团伙的名字、头儿的名字、工作的地方告诉了市局刑侦队,要刑侦队去抓人。刑侦队没找着那人,就把纸条扔在抽屉里没管。第三天,黑帮又卷土重来,把那家全部砸烂。我在电台里又听到呼救,局里其他人不在,我就一个人开车去了。到那一看,村边站着两个机场分局的民警,他们见我来了,说里面危险,别进去。原来他们路过此地时,案件正在发生。村里人看来了两个警察,不但没跑还拿着刀要砍他们,吓得他俩跑到门外来用电台呼救。我一听,气得够戗,踹门我就进去了。一看,人已经从后门跑掉了,地上全是血。我就开车追,当地的路很不好,开车很难追,就给他们跑掉了。 对这个事我很生气,本来这个案卷我做得很好,就等市局刑侦队去抓人了,结果他们没抓,案子就进一步发展了。我又写了份报告,措辞比较激烈,说他们已经威胁到帝力市两个警察了。帝力市局比较重视,当天派了两个警察来,让我们协助他们搞这个案子。这两个警察都是从大国来的,不大了解当地的情况,见面就说先找村长谈谈。我说,我认识村长,恐怕他帮不了什么大忙。他俩说,那不,你得尊重当地的领导人。得,我们就去见村长。村长说,没问题,明天早上我把他们都带到村公所,你们来带人就行了。两侦察员很高兴--这不挺容易嘛!我知道说别的也没用,只好说,行,明天我跟你们一起来带人。侦察员走后,我就开始查黑帮的头儿在哪儿。 第二天,我和侦察员到村公所,等半天不见村长,只来了个村长助理,说昨天晚上村长找那些人去了,那些人都跑了,村长今天去埃留找游击队了,找他们来逮捕这些人。我一听就知道在瞎说,只有先稳住他。我说,好吧,村长回来你跟他说,我们下午3点再来。 两个侦察员很沮丧。我就把报案人和巡逻队都召到一起,到工地上找那小子。结果他没在。当地人多年来受外国人统治,形成一种强烈的观点,不给任何外国人报信,一听说我们要他们带路,大家都干活去了,没人理我们。 后来我给老板做工作,说这人昨天没参加打架,警察找他是让他把情况说清楚,要不每天找他,他没法儿上班,日子也不好过。老板就带我们去了。到他家一看,号称去找民兵的村长正在他家门口坐着呢!我在门口一听,里面有人在洗澡,就马上要队员把房子包围起来,"一个也不能跑!"说完之后,队员都瞪着眼看我--我一着急,用的是中文! 围起来后,就问村长:埃留离这儿很远嘛,你这么一会儿就回来了?村长不好意思了。后来从屋子里抓了两个要犯,被关到监狱里了。从此这个团伙就平息了。 中国维和民警"一炮打响" 当巡警时我曾经一个人平定过一个骚乱。那次是红十字医院保安为了增加工资,罢了工,还带着武器把医院整个都封了。接到报警我们只知道医院发生问题了,也不知道什么事,我就和另一个民警开车去了。到那里一看,医院门口站着四五个汉子,个个都拿着武器拿着刀,那个民警就直哆嗦不敢下车了。问我要不要回去多叫点儿人?我说,叫什么人?叫咱们来就得进屋看看究竟怎么回事儿。他说,不行我肚子饿了要吃点东西。我说,行了,你就在车上呆着吧,说完就一人进去了。找到保安的头儿,他提出要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又找到医院的头儿,医院不同意他们的条件,而且医院说如果现在答应了,保不齐他们以后什么时候又会这样武力威胁,医院就没法开了。双方谈不到一起。 后来,我把保安叫过来,说,现在给你10分钟出去先把人撤走了,把医院大门打开,让病人正常看病,否则马上调人来把你们都抓起来。保安说,病人进可以,但医院的管理人员不能走,尤其是医院的行政主管不能走。他跑了我们怎么办?我说,他不会跑的,他是联合国的人他怎么跑?我又回头找医院的头儿做工作。最后把双方拉到谈判桌上,达成了折中协议,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当地,由劳资双方引起的暴乱骚乱很多,我成功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市局对此比较赞赏,所以两个月时我已经有点名气。后来我出任科摩罗分局局长后,我那里也没有因为纠纷而引发更大规模的骚乱。 由于在分局干得不错,有很多升入更高职位的机会。后来由于条件改善,有的办公室有空调了,我那里一直没有空调,帝力那么热,在有空调的办公室里工作肯定很舒服,但我一直就想,我们第一批派出的民警不多,要想增加影响,坐在办公室里不接触群众,人家东帝汶人怎么知道你在维和呀!坐在办公室里,是显示不出作为一线警察的高素质的。我做了近十个月局长,吃了不少苦,但觉得工作有意义。 在UN,从民警总监到普通巡警,拿的是同样津贴。UN的晋职机制比较公开公平。有空缺职位就贴出来,每个人都可以申请。我们第一批15位民警,不是所有的都有晋职,但所有的都干得不错。在UN职务并不代表业绩。我们有个侦察员,一去就很快被任命为队长。后来因为他是搞侦察的,愿意和国际同行多交流交流,主动要求调到又苦又累的侦察队,他工作非常出色,多次受表彰,后来在重组时,我曾考虑调他过来,给他任职,但帝力总局一直不放他,觉得他干得太好了。我也多次说,我们不一定都要去争取职务,只要每个人把本职工作做好,得到其他国家民警的认同和尊敬就达到目的了。 因为出发时部领导反复说,要一炮打响,为以后派出做准备,所以无论对自己还是队员,我要求都很严。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派出,第一次形成印象后,很难改变。正因为第一批干得比较好,条件也成熟了,我们就到UN总部向主管人事的官员提出增派人员的愿望。后来通过国内的努力,我们又派了40个民警。那边说,像我们第二次增派这么大规模的很少,但由于我们第一批干得比较出色,中国民警在任务区比较受欢迎。(转自《中国青年》) |
|||
|
|
||||
主编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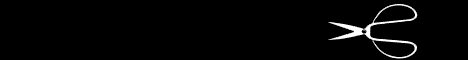 本网站所刊载信息,不代表中新社观点。 刊用本网站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
|